我想吃掉你的腸臟
「多物種台灣研究在北美」的可能性
一個週日的早上七點,我走過人煙稀少的街道,按著美食部落格的指示,從一個不起眼的路口轉入巷子。巷內提供各式服務的店尚未開市,遠處可見幾張桌子,在白燈的照射下,在光線微弱的小巷裡顯得特別注目。快步向前走,我很快到達目的地:一間專賣虱目魚料理的小店。
「麻煩你,一碗魚肚漿湯、一塊煎魚肚,一份魯魚頭,呀,也想要燙魚皮。」說起虱目魚,我立刻如數家珍。
「請問現在有魚腸嗎?」
「有,要煎的還是燙的?」
「那要一份煎的吧。」
冷靜的回答掩蓋不住我內心的興奮。期待而久的高雄鹽埕虱目魚腸,今天終於吃得到了!坐在桌子前的我沒等多久,就和巷子內其他饕客一樣,看到小店員工把熱騰騰的虱目魚美食端到我面前。
當然是相機先吃。

一魚多吃
我在進行田野研究時偶爾會吃到虱目魚腸。我的田野地點思慕村位於台17線上,是虱目魚的集散地,供應嘉義以北的消費市場。 由思慕村的魚販(當地稱為魚行)收集到的魚通常都是整尾被泡在盛有冰水的保麗龍箱,由司機運送到都市的消費地魚市場。另外的一些魚則是在初級處理加工場內,被工人分切成魚頭、魚肚、魚皮及魚背肉,除了在魚市場交易外,更多是直接被送到菜市場、超市及虱目魚專賣店。魚鱗及骨頭則成為魚飼料的原料。
魚內臟通常都被處理場內的工人丟到盤子內收集,作為飼料的原料。但是,我也目擊工人把少量內臟帶回家烹調,其中,我曾站在一旁,觀察著一位工人把虱目魚腱取出。她跟我說,市面上很少出售這種產品,她快下班時,就先從盤子裡找出魚腱,帶回家作午餐。
沒有走進處理場,我大概不會知道思慕村的村民對虱目魚有這麼細緻的了解,也吃得這麼講解,追求的口感是這麼的細膩。事實上,虱目魚除了鰓和魚骨外,幾乎所有部份都可以用來吃,除了魚頭、魚肚,魚皮(連著一塊肉)可以用作涼拌或煮湯,魚腸和魚腱是饕餐的美食(delicacy),連著小骨的肉,則用作魚丸及魚漿的原料,魚背連鰭的部份,現在已被開發為「魚嶺」,用來香煎,成為下酒菜。連魚鱗都可以煮成膠原蛋白豐富的果凍,不過非常費工,一般家庭不會特別花時間製作這個食品。

我對虱目魚的參與觀察,除了站在一旁看外,當然也包括把牠吃掉。有時,漁民會在收成後,送我一兩尾虱目魚。回到住處,我就走進行廚房,拿起刀子,手忙腳亂地練習開魚肚,把內臟抽出來,然後切開魚肉及魚頭,燒紅了鍋子,學習把魚肚煎得香脆可口,其餘部份全放到熱水中煮湯。當然,也會把魚腸稍為清燙一下,作為小菜,
魚腸的產業鏈
準備結束田野,離開台灣前,我騎著機車,在台南、高雄及屏東三個縣市進行訪談,有時早上在街道上尋找牛肉湯,和鄰座的大叔們一起捧著魯肉飯,喝著牛肉湯。這種很地道的早餐店,除了美食家外,人類學家也很欣賞。虱目魚店也一樣,早晨時份,當地居民來到專賣店,享受著虱目魚料理。在專賣店吃早餐是在國外看不見的風景,也是晚起的研究者收集不到的田野資料。幸好我被漁民們訓練久了,大清早起床對我來說不是什麼難事。
回到楓葉國後,我時常會把購自亞洲超市、整尾冷凍虱目魚退冰,繼續練習我的切魚肚及料理技巧。在論文口試結束後,老師及同學為我舉辦了一場慶祝派對,弄了一整桌台式夜市小吃,還現場表演幾塊煎魚肚。為免嚇跑他們,我把有骨頭的部份及內臟留在家,自己消化掉。


可是,冷凍虱目魚裡的魚腸總是讓我覺得不好吃,無論是香煎還是清燙,我都找不回在台灣吃魚腸時的味覺感動。

究竟是哪裡出差錯?
其實,我早在田野就收集到答案了(只是在國外不死心就是想吃掉腸臟)。
時間回到2015年的3月,我在高雄市的一個漁村訪問一位以虱目魚一夜乾作為產品出售的商人,他向我介紹了當地的販頭A,我們就在魚塭的工寮內邊吃午餐邊聊天。販頭A說道,他們主要進行「暗撈」,即晚上進行捕撈,目的是透過在地的魚市場,供應新鮮的魚獲給高雄地區內的專賣店及菜市場等。這跟我在思慕村看到的作業時間不同,我當然後希望能去紀錄。
「我今天有事,明天晚上可以回來看收成嗎?」
「可以,我們每天都抓魚,你就下午六、七點回來這邊!」
鄉下地方的約定就是爽快(政治不正確的人類學家)。第二天傍晚,我就再來到村子裡,站在一旁看著作業流程,一邊利用我在思慕的經驗,比較兩個地方的不同。有趣的是,這裡除了負責撈魚的工人,以及依據大小替魚獲分級的工人外,現場還有五位工人,坐在空地上,手拿著電動工具為上岸後的魚獲去鱗。然後,變得光滑的虱目魚被放到膠籃子裡;跟我在思慕村看到的不同,膠籃沒有注入大量冰水(思慕村的魚行使用保麗龍箱),就直接被搬到貨車的冷藏庫中。


販頭A:「我們的做法和思慕村的魚販不同,他們利用保麗龍箱來放虱目魚,上面放很多碎冰,這樣送到台北時,魚貨還算是新鮮。我們的市場就在高雄,晚上把魚抓起來,去鱗後,就可送到魚市場交易,專賣虱目魚的攤販從早上三點就可以賣魚了,連腸子都可以吃。冰過的魚,其腸子都變硬,都不好吃了。」
和工人們在工寮中吃過虱目魚粥作為宵夜後,我就騎車到附近的魚市場中,追蹤這些魚的下落。凌晨五點,我隨意找個路邊的虱目魚專賣攤坐下來,打算先吃個早餐,再去找另一個地方的深水虱目魚養殖推動者進行訪談。
結果,攤販跟我說:「魚腸已經賣完。」
高雄的饕客有這麼愛吃虱目魚腸嗎?
對這項美食念念不忘的我,在畢業後來到台灣工作,出差高雄時總是到鹽埕的巷子內,到訪同一間小店,大開朵頤。今年初來到台東工作,經另一位人類家介紹,我知道學校附近就有一間以虱目魚菜式聞名的路邊小店。為了吃到魚腸,我曾經多次到訪該店,每天都問「今天有魚腸嗎?」結果分別是:
下午:「魚腸賣完了,你中午前來吧。」
中午:「魚腸賣完了,你十點前來吧。」
上午六點半:「魚腸還未到,你七點半後來吧。」
唯一一次吃到魚腸的時候,是早上八點多上班前的早餐時段。

我認為,台東縣並非虱目魚的產地,魚貨從產地運到當地需時,而魚腸隔天不好吃,因此,就出現了一個經店家計算過的銷售時間:早上七點半到十點。這和我在其他地方「田野經驗」出現地域性的落差。那麼台北呢?我曾走進不同的虱目魚專賣店,都未曾成功「捕獲野生魚腸」。
北美台灣研究:多物種的轉向?
好了,要進入本文的第二部份:北美台灣研究學會(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下稱NATSA)了。虱目魚和NATSA的關係在哪裡呢?看倌們先不要心急,適逢NATSA二十五週年,讓我從當年說起。簡單而言,NATSA剛開始是由一群在北美留學的研究生組成的組織,起初活躍的成員,現在都事業有成,有些是大學教授,有些是政治人物;聽說他們當年希望在國外,都能為台灣找尋出路,因此以研究生的力量,成立學會。李宜澤老師在2014年曾寫了一篇芭樂文〈北美的台灣在哪裡?記二十年的「北美台灣研究學會」〉,描述NATSA的早期到中期的轉變。該年也是我首年加入NATSA成為幹部,後來我們成為慶祝NATSA二十週年的書籍《跨界跨代的台灣研究-北美台灣研究學會(NATSA)二十年》 的作者之一。當時,我和另外的作者們提出,NATSA已成為台灣研究領域中,行動公民的學術人才庫。今年,我擔任會長,主導學會的發展工作。和外界一般的印象不同,NATSA團隊早已不是純粹由研究生組成,目前不同階段的學者、研究生及業界人士都有各種程度的參與,共同維持NATSA的活躍度及前瞻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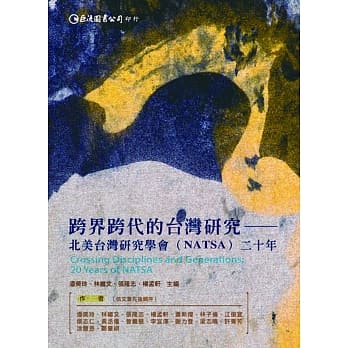
在學會發表的文章,早期以政治科學、社會學為主(見跨界一書中林子倫、江俊宜一章)。在2006年後,文學類的文章成為另一大類。值得留意的是,人類學背景的幹部在2008年後成為主力,會長計有曾薰慧、李宜澤及我,會議議程統籌自2011年起包括郭揚義、Derek Sheridan (謝力登)、Matthew West (魏仲然)Spencer Chen及我。以會議議程統籌之言,會長願意把此重任交予人類學背景的幹部,除了行政能力外,也是因為我們的研究比較能和政治科學、人文學科及社會科學同時對話,因此很適合NATSA的學術需求。
我從2014年加入團隊至2016年較為活躍,至2018年成為會長,在這幾年來,可以對北美的台灣研究社群進行一些深入的參與觀察。其中,我發現NATSA是一個頗為「以人類為中心」的學術平台。或許因為歷史因素,NATSA一直以台灣作為國家(State,不管是什麼程度上的)的主體性作為終極關懷。過去會議的主題(見李宜澤的文章)都嘗試為台灣的前途找到定位及出路。因此,會議上發表過的研究文章,大宗也是相近的題材,探索台灣人的政治處境、身份認同、被(後)殖民經驗等。雖然近年在北美的學術討論趨向科技與社會、後人類、人類世等題目,但NATSA能夠召集到的相關文章少之有少。針對這一點,我曾組過有關海洋的發表小組,邀請一位海洋科學背景的夥伴加入,她也擔任過學會的幹部。但目前看來,其他的幹部、會議文章及主題活動,都以人類為研究主題、對象,進行的討論,就台灣「人」的經驗。

台灣內外的動物、植物及死物的經驗就是如何呢?我認為NATSA的平台上,目前還缺乏「牠/它們的聲音」。因此,我倡議的是參考人類學最近在實驗的「本體論的轉向」,說得再簡單一點,就是要重新思考台灣研究與非人類的關係,在NATSA的平台上,鼓勵「多物種」跨領域的討論及發表機會。
觀乎以台灣為對象的研究中,我們不難發現更多以「去人類中心」為思考方式的人類學文章已經發表,如蔡晏霖的研究,而台灣的人類學家也進行跨文化的相關研究(如趙恩潔),亦跟社會學及地理學不少走相近路線的人在會議發表上有所合作。在2018年的NATSA年會上,社會學者劉仲恩與我不約而同地呼籲NATSA應該多鼓勵「去人類中心」的研究在會中發表。事實上,在2016年多倫多年會中,某位演講者提出 “Taiwan Studies is getting boring”後,人類學者Scott Simon在其閉幕演講中,提出了Formosana Studies,希望大家能跳脫出台灣研究的框框,以跨太平洋的思維去理解台灣。他近年的研究,也是以台灣漢人及原住民各自與狗的關係,進行比較。他的喊話,對現場的人類學者來說,好像已經是研究經驗的一部份,但對政治學者、人文學者及部份社會科學者來說,是一個相對新近、突破框框的思考及研究方式。
我在NATSA的參與觀察,包括把一眾在不同領域各壇勝場的夥伴,帶到台灣的田野中。我們去看魚塭、曬鹽場,在私下的聚會中,我煮了一些虱目魚的菜式分享。在去國家公園遊玩的車程中,他們被困在車子上聽虱目魚的生命史(我博士論文有七章和虱目魚直接有關,每章講一小時,時間過很快)。夥伴們的回應通常是:「怎麼你好像比我們台灣人還熟台灣?」
現在從NATSA的發展方向出發去回想過去做過的事,我方才發現北美台灣研究很缺乏從物出發的全觀研究。我認為虱目魚是可以和Scott Simon的狗研究比較的一個好例子。如果我們不透徹理解虱目魚的物性,例如腸臟易腐敗的生理特質,甚至在魚塭裡牠們被餵什麼,活在什麼樣的水生環境中,那麼我們很難探討產業內不同的人類行動者如何組織他們的工作團隊,更別說要了解他們如何設計養殖、收成、處理、物流及零售水產的流程。更甚之,沒有適度的田野經驗,我們大概也不能理解飲食文化如何受到生物特性、地域、時間、交通設施的影響。
目前我認為活躍於北美的台灣學者較缺乏以「物」為對象的研究,有兩個主要原因。首先,區域研究本身就是以人、國家及空間來設界限的,要進行跨物種的研究,有時候要先打破「邊界」。過去台灣研究的討論中,邊界卻是重要的一個環節:台灣/中國、台灣/日本、台灣/韓國等,無不是先立一個「邊界」,再探討、比較社會現象。「物」卻可以是很流動的實物及概念,例如非洲豬瘟,就可以隨著豬屍在海上飄流;鰻魚、烏魚等迥游性魚種,又是跨國界的議題;就算是成為商品的台灣鯛,在包裝被拆下後,消費者不會知道其來源地。因此,NATSA以區域研究自我設限,難以吸引到的跨物種研究。另外,對於非以田野工作為主要或其中一種研究方法的學者而言,「以物」為對象的研究彷彿是天方夜談,在NATSA的場域中,跨學科、團隊型的研究文章幾乎沒有出現過,個人發表是主流方式,因此,實在很難找到非人類學、地理學及社會學的學者或學生以「跨物種研究」為發表方向。
我認為「跨物種研究」應是NATSA及北美台灣研究學界有待加強的部份,簡單而言,從物出發,我們可以看到更多元的台灣。我在研究時常常聽到一句話:「台灣人都很愛吃虱目魚」。這個是在比較「台灣人」與「非台灣人」時會用上的簡化版身份認同,當我們更細緻地去理解虱目魚和台灣(研究)的關係時,我們可以看到跨族群的文化、地理差異。魚應該是沒有國族身份認同的,在國外,虱目魚就是虱目魚。但是,包裝上寫上的產地,以及調味方式,彷彿又為虱目魚掛上「國家」的標籤。


當虱目魚作為商品外銷,我們又能看到冷凍與否,虱目魚都可能成為「非台灣文化」的產品。在加拿大的冷凍虱目魚,其腸臟的品質跟供本土消費的同類不能比較。魚的特性、跨國經驗及台灣人(尤其是南部)的身份認同,就在虱目魚腸的「美味性」的討論中呈現出來了。
多少移居海外的台灣人,為了一碗魚腸湯,下飛機後就去搜尋虱目魚專賣店?
政治方面,在ECFA契作影響下,曾以冷藏(保麗龍箱、冰水保鮮)方法賣到大陸的台南虱目魚,我相信其魚腸不可能吸引挑吃的上海人。利用虱目魚發大財、拿選票的政客,還是要多多觀察虱目魚的生物特性,才有可能達到其政治、經濟及文化目的。沒有吃到同樣品質的虱目魚腸,如何兩岸一家親?
當北美研究社群在利用民調、選舉材料、媒體、歷史及訪談資料理解台灣的主體性時,我認為人類學者及其他夥伴們仍然能進行田野研究及進行民族誌式的書寫,呈現出全面以及多物種的思考方式,與夥伴們一起開拓台灣研究更多可能性。藉此,我們也能把「為台灣為國家」及「人為中心」的舊框框打破。這不就是人文學者、自然學者及社會科學者應該自身任命的學術責任嗎?NATSA作為跨學科的學會,更應推廣這種研究取向,加強台灣研究的多元性。
區域研究重新以物(不管是動物、植物、死物)來串連,是我為於五月西雅圖年會中慶祝二十五週年的NATSA許下的生日願望,也是我對未來台灣研究的期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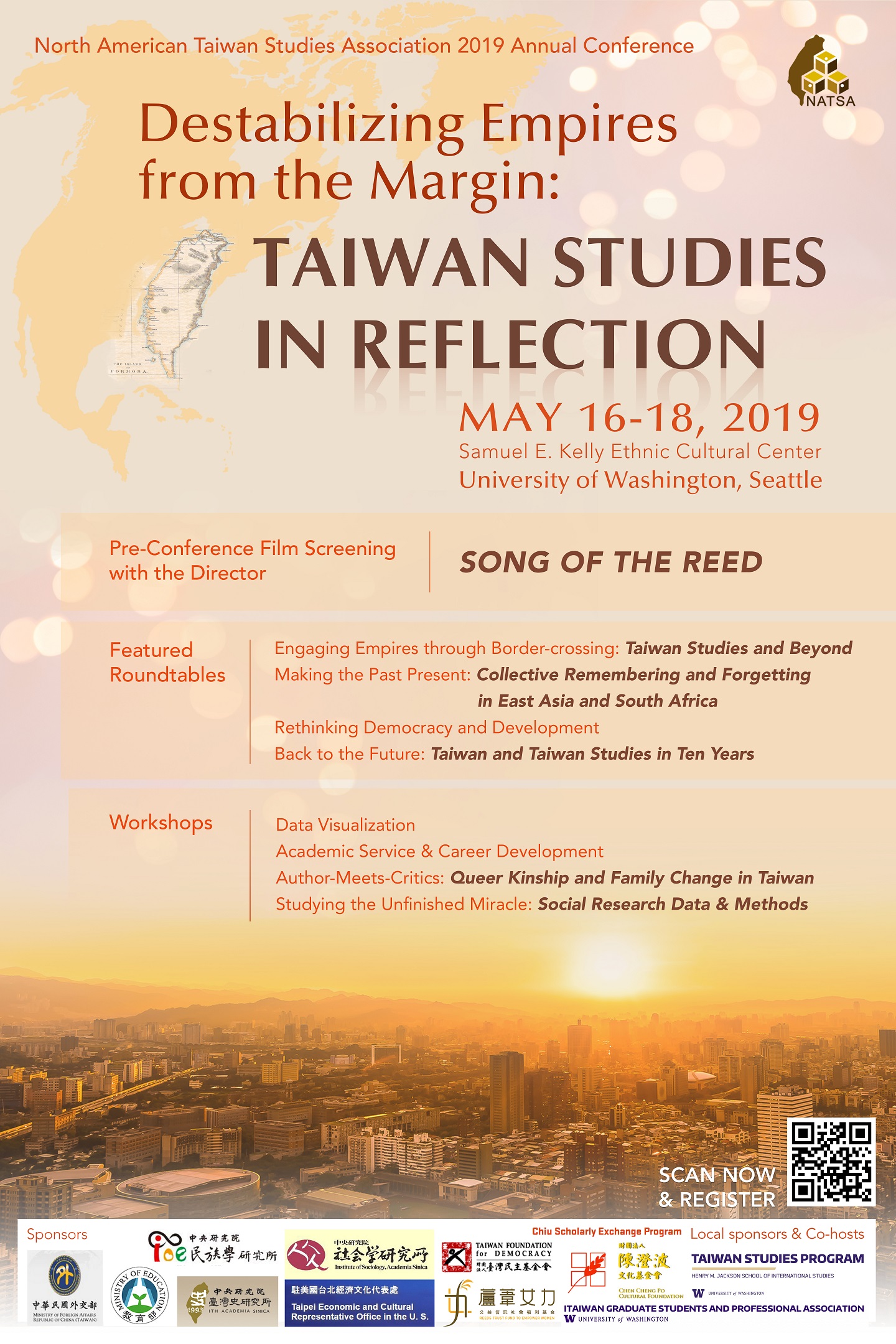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鄭肇祺 我想吃掉你的腸臟:「多物種台灣研究在北美」的可能性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index.php/article/6714 )



回應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虱目魚腸用煎的太可惜了!應該用燙的。我所知高雄市鹽埕區瀨南街144-1阿貴虱目魚料理做得很好吃。台北是吃不到新鮮的虱目魚的。說道魚腸料理,全世界最獨步的莫過於廣東的雞疍油條蒸(草魚)腸。香港的中式飯店尚可吃到。網上找找看吧!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