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到AI(Articulated Indigeneity)
如何在人工智慧裡與原住民族對話
從人工智慧(AI)開發成為人類的知識夥伴以來,開啟許多熱鬧的討論:不管是對於正面地看待人類生活如何因此變得便利且迅速,學習模式因此可以進行快速的變化而不受環境與階級的影響(如同網際網路一開始出現的樂觀預期);或者是反面看待人類活動被替代的比例,從未來的演變返照現在的過度開放等等。這一切都說明AI的發展在人類歷史裡面,開啟了因為用火而打開智能開發的另一限度之後,又一次的跳躍進展。AI作為智能工具的火熱討論,在教育環境裡也有許多深遠的影響,有好幾位學界的朋友已經感受到AI引發的震撼教育。例如在課堂期末繳交作業時,多半已經不能夠以過去常用的蒐集資料書寫單一讀書心得的方式處理,轉而走向使用申論題,並且給予特殊條件才能答對的題型,來避免學生使用AI或者相似的語言模型例如ChatGPT來回答問題,代替真實的閱讀與思考回應。
但是,AI並不是知識的敵人,作為當代最主要的知識工具,對AI的認識與重新思考可以作為思考人類學知識的出發點之一。AI把人類的智慧模式,從散亂在網路各地的內容,轉變為集中於問答形式與創作指令的操作;另一方面,AI輔具的出現,也重新讓人界定「具備知識的行動個體」是否不再是由人類所獨佔的能力。詢問ChatGPT:「請問人類學與AI的關聯有哪些」,主要的回應有四項:1. 文化與社會影響 2. 技術的接受與拒絕 3. 倫理與價值觀 4. 技術設計與應用。這四種回應,其實也可以看成人類學與STS(科技與社會研究)交會時最主要的四個主題。這幾個主題把AI當作反思人類學與技術之間的「連結橋樑」。社會學者林文源與清華大學的物理學者王道維合作的計畫,在推動AI教學的道路上不遺餘力。以人文社會課程用生成式AI指令範圍網站,討論如何將AI教學使用公共化。依照林文源老師廣發的人社AI指令協作邀請函,其目標在於「積極由高教課程拓展AI共善的可能性:藉著融合人社老師課程的設計與Ai能提供的線索(並非答案),拓展新的教與學的方式。而開發指令集並開放給社群,一是為了集思廣益,也是為了強化AI時代教育發展的公共性」。其中包括了,通用型、大數據資料、跨領域協作、哲學邏輯、歷史學習、AI法律政策、醫學人文、社會文化、科技與社會等多層面的分析。透過眾人協作的集合方式,試著將AI的影響力在教育環境裡發揮最大效應。
在一篇非常濃縮的著作裡,人類學者Chris Salter與Alexandre Saunier(2023)認為,「人工人類學」(Anthropology of the Artificial)可以連結媒體,策展,與文化再現的多元型態,但是也需要多層次的反思。從混生(hybrid)來看人工人類學的議題有三大方向:其一是對於現代憲章的分類破除,其二是討論分配於人類啟動技術物與系統之間的能動性,包含各種時空規模交錯的「基礎設施」,最後是如何從感覺再現的狀態下,重新討論殖民對於身體轉換或者生物有機體的模擬情境,以及如何從「製造」的角度來理解人工機制的行動而非「生成」。從這個角度來看,人工型態的人類學研究對象,是如同Lucy Schuman所說的「人工科技下的展示行動者」(performative agencies of the techno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到底「人工為何物」成為論述人工人類學時的重要核心。延續「文化」與「自然」的二元對比質疑討論,以「多於人類」(more than human)的層面出現,包括女性主義STS研究取向延伸的新物質論(new materialism),多重本體論觀點(perspectivist),多物種(multispecies)等等轉向,以用來反思人與物質在本體論上的差異論述。
即便這些努力,仍然有些未解議題:第一,從歐美生物性觀點下繼承而來,對比於那些無生物的「非人類」,對生物形態的多物種成員的偏重與強調,例如孢子,昆蟲,樹木,植物等等。在這個情境下,來自於民族誌反思的描述技術,多半針對的是可與人產生共通「生命」的非人;而需要配合數學與技術物質討論的「技術誌」(technography)卻難以被化約地存在於認同,社區,國族,能動性與主體性等等議題裡面。其次,在人工的概念裡,面對人造物的內容不該只是計算程式。程式所包含的部分不只是指令程序,還有許多包含聲音與多種模式的狀態(例如被駭客入侵或者再程序化),而這些以前都只留存在黑箱系統裡面。第三,對於「人工生命」或者人工智慧與傳統自然科學(以及衍生的民族誌)的差異是,自然學科強調如何描述對象「如是」,但人工智慧(因為設計的延伸)強調描述對象「應該如何」。回應前面這三個層次的討論,對於AI的反思除了針對新型態的人類社會智能化以及模擬操作環境之外,還增加了民族誌的反思狀態,研究協作對象的公共化與解黑箱化,以及面對設計的創作潛能而不只是描述狀態的新任務。
有趣的是,反思AI研究在現代社會的路徑,竟然與原住民知識體系以及其知識運用的方向有奇特的類同。人類學對於知識與持有者的討論,來自使用象徵與再現政治的多樣性。這些多樣性包含在運用知識的主體對象不同,使用知識的情境差異,以及透過已有的知識與更大的創作脈絡相連結等等。主要在於對於原住民知識認識角度與科學知識相較,有以下幾種差別:

圖片來源:作者自製
從「知識架構」,「知識持有者」,「知識型態」到「知識應用時機」,原民知識與科學知識有明顯的差別;主要的不同在於面對知識對象,以及所知的時機與型態上面,兩者對於如何應用有明顯的差別。但這裡弔詭的地方是,AI應該是針對西方科學知識出現的「應用操作者」,但「具有AI情境的知識互動」(如同我們在前一段落討論到的,卻與「原住民知識」有極為相近的操作方向。主要的因素可能在於AI人工智慧與原住民的關係有下面三種相關性:其一,是否把某種具有認知能力的操作稱為「人」或者「非人」,AI的出現與原住民的認識論相近。作為可能的知識對象,甚至稱之為兄弟姐妹的親屬類別,在原住民的分類系統中並不像非原民那樣狹隘;不論是自然界的動物類別,甚至石頭或者瀑布的「地景」,都可以稱為親屬。因此在所知者的認識當中,原住民的親屬認識論,就可能把AI包含在其中。其二,原住民傳統敘說情境的知識發展,多半仍然根植於「口語表達」。因為這樣,從口語對話中出現的敘事類型,例如故事,傳說,對話錄,寓言等等,都是AI在回應人類問題時常用的表達方式,也因此呈現出AI與原住民知識情境可能的親近關係。其三,原住民與AI在特定的文學情境上,有類同的展現;也因此對於「擬人化」的思維有類似的選擇性。
例如在原住民智財權律師Karina Kesserwan(2018)的文章「原住民知識如何形塑我們對AI的了解」中,就提出當美國原住民(例如Iroquois族群)提到當前的行為必須為七代之後的子孫負責,所提出來的想像並不是七代的實體子孫,而是如同更新版本一樣的AI 7.0概念,必須要從第一代開始開放使用知識的方式,而重新理解永續的可能性。在原住民的知識領域裡面,對於尚未覺察的事物進行多方面的探索,是生存的基本能力。例如在Inuit語言裡面有iktsuarpok這個字,意思是對於「未知的覺察讓人向外探索去看看有沒有趨近之物」(Kesserwan 2018)。這樣的動能必然與原住民的生活息息相關,以便對於環境的危險保持高度警戒,但當然也透過這樣的覺察發現新事物的型態。而對於新事物的認知,看似與傳統熟悉的議題成為對立;但恰恰相反,具有了解新事物的能力,才能夠將現有知識應用於合適且對應的空間。

Kesserwan, Karina. 2018. “How can Indigenous Knowledge Shape our View of AI”
讓我們回到AI的實際操作。如果問ChtGPT「你認為原住民族在哪些層面會應用到AI」,會得到這樣的回答:
- 語言保護與傳承:許多原住民族擁有獨特的語言,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語言可能面臨消失的風險。人工智慧可以用來開發語言學習和保護工具,包括語音辨識、機器翻譯和語言學習應用,幫助原住民社區保護、傳承和教導他們的語言。
- 文化遺產保護:人工智慧可以用來數位化和保護原住民族的文化遺產,包括傳統藝術、音樂、舞蹈等。透過數位化技術,這些文化遺產可以被記錄、保存和傳播給後代,同時也可以在全球範圍內分享和展示。
- 土地管理和環境保護:原住民對他們的土地和環境有著深厚的認識和連接,他們的傳統知識可以幫助更好地管理和保護自然資源。人工智慧技術可以用來分析環境數據、監測野生動物遷徙、預測自然災害等,幫助原住民更有效地管理和保護他們的土地和環境。
- 社區健康與福祉:人工智慧可以用來提高原住民社區的醫療保健服務和社會福利。例如,智慧健康監測系統可以幫助監測老年人或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狀況,智慧輔助技術可以幫助殘障人士更好地融入社區。
這些回答看起來非常正式,也的確觸及原住民族常見的一些問題。但如果我們更仔細的閱讀,也會發現這些回答多半是針對原住民族目前已經有的議題來回應(語言,文化遺產,土地與環境,健康),把解決辦法和人工智慧連結起來。這樣說起來,好像也沒有說出什麼不一樣的地方?沿著ChatGPT的說法,我認為至少AI與原住民的關係大概有五種:原住民與AI的關係:大概可以有五種。第一個是作為資料庫。 第二個是作為知識與情境模擬的介面。 第三個是知識建構的在地模型。 第四個是社會媒介與新環境的鏈結。 第五種作為原民文化的創作來源。
如果我們滿足於前面的觀點,的確會感到無所差異的錯覺。但如果對於知識的情境進一步推敲,我們可以從語言象徵和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待AI帶來的原住民知識觀點:人工智慧設計與原住民知識相關的方向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協助探索的覺察能力,透過人工智慧組合去開拓與原住民情境相關的知識處境(從符號學觀點來說可以是「能知」the knower),比如在都市環境如何運用原住民知識。一類是在資料收集之後的「後設資料庫」Meta Data的概念,亦即如何將所取得成為知識的內容加以分類,形成特定知識體系(也就是「所知」the known的範疇),像是如何以阿美族語言表意物理學觀念。這兩者都觸及到一個在原住民知識情境下的特定需求,那就是「資料主權」(Data Sovereignty)。
「資料主權」可以說是繼「土地主權」,「文化主權」之後,原住民主權系列的第三股湧浪。主權的內涵當然是回歸到「自主的權力」與「獨立的意識」這兩部分,但不只是關於「自主的權力」可能受到歷史情境的影響而缺乏實際被肯認或者可能執行的場域,關於「獨立的意識」更受到知識在殖民化之後如何表達解殖民能知,以及與政治認同的對比等層面來思考。這個議題在2015年時於澳洲坎培拉進行過第一次英國殖民區原住民族的「資料主權」會議,並且集結成了《原住民資料主權:朝向未來議程》一書(Kukutai & Taylor 2016)。書中的導論開宗明義揭示:「資料主權指向廣泛的新興議題,從資料儲存的法律與倫理層面,擁有權,存取與知情同意,一直到智慧財產權與資料如何在研究脈絡下運用的實用層面,政策與操作方式等等。。。同樣的,原住民資料生態系也可以說包羅萬象,從原住民社區與組織,原住民政府,公共機關,跨國政府機構,非政府組織,研究單位,以及商業個體等等對於資料的持有使用。」該書的討論範圍主要在於「資料主權的意義,殖民對原住民資料主權的影響,一直到如何對原住民案例當中的資料主權給予實用且合乎原民期待的操作方式」(ibid, 5)。其中四大部分的討論包括了:第一,討論資料主權的歷史成因。第二,對現行後殖民統計系統持續的批判與反思(包含對澳洲5D data的批判:disparity 不平, deprivation 剝奪, disadvantage 劣勢處境, dysfunction 無法運作, and difference以及差別待遇)。第三,第一次集結了英國移民墾殖文化區(CANZUS)裡面不同地區和原住民族對於自我文化資料主權的伸張策略。第四部分,則以澳洲和紐西蘭當中,國家統計局等單位如何收集與生產原住民相關統計資料並加以討論為主。透過總共這四個部分與不同歷史和政治經濟情勢下的回溯討論,現有統計資料的生成以及內在邏輯,將原住民的資料主權之形成過程「逆其紋理以爬梳」(read against the grains),以達到更近一步的揭露與再次面對行動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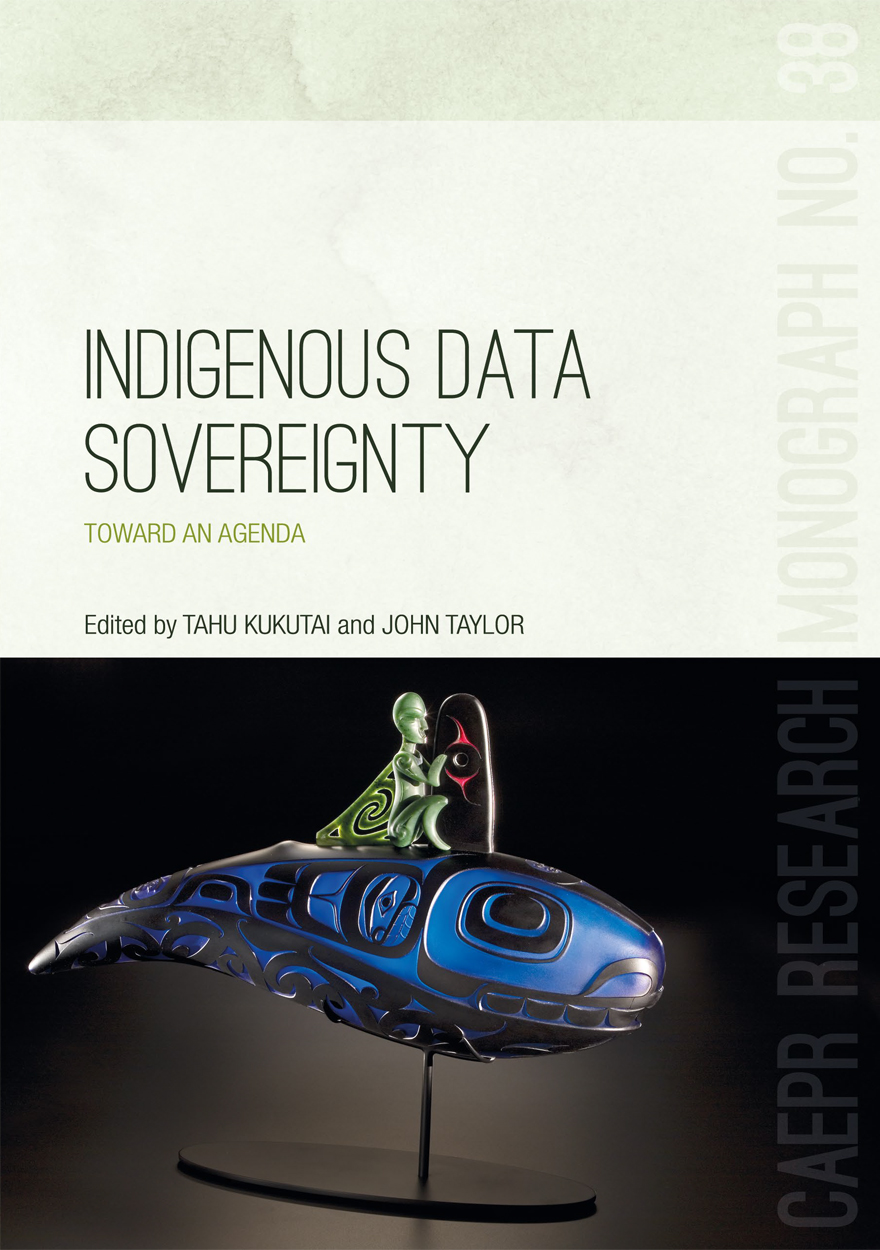
Kukutai, Tahu, and John Taylor eds. 2016. Indigenous Data Sovereignty: Toward an Agenda. ANU press.
而最近一份相關的出版品,則是由紐西蘭毛利族人所出版的《毛利敘事與資料主權》(Storying Maori and Data Sovereignty: The intersections of whanau narratives and sociopolitical theorising)。這本書由奧克蘭大學的講師Kiri West所收集,並且由Te Atawhai o Te Ao Charitable 信託法人的執行長Dr Rāwiri Tinirau所編輯。是一本為了毛利族人自身需求所編輯的工具手冊。透過這份小手冊,毛利族人以故事敘說的方式,向族人說明在哪些經營管理,資訊交流,或者是文化採集的層面上,會碰上IDS(原住民資料主權)的議題,並且要如何保護自身的資料主權完整,或者如何透過敘說的環境共生與多主體模式,讓資料不止於一個敘說者,而讓文化知識的主權得以保留在毛利人的文化使用場域裡。例如關於一條河流的流域與環境的描述,必須要取得引用在地詩人與該地生活住民的地名與物種名稱的權利,而運用這些知識的權力是保存在當地單位或者敘說者身份上,並不是國家統計局可以單獨完成。某個程度上(雖然資料密度完全不同),也許可以與加密貨幣對話,甚至發展成另一種文化敘說職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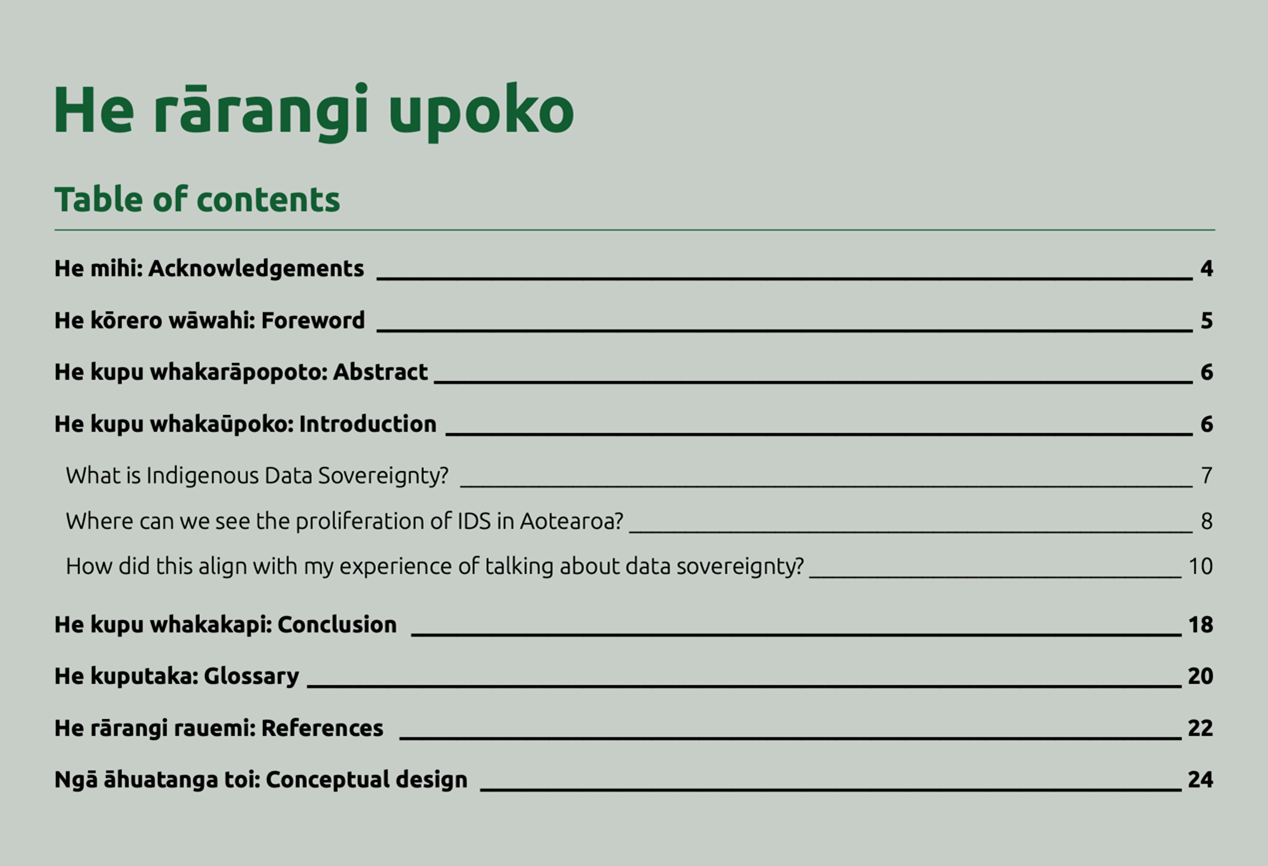
從在地深描的資料回頭來看,最後關於AI的一個隨想,是最近關於Artificial Indigeneity的說法。這個說法是由文學研究者引伸出來的。不久前在中研院的人文與社科中心有一場演講,講題是”The New AI (Artificial Indigeneity): The Rise of Indigenous Speculative Fiction in Taiwan”. 講者是在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任教的張迪涵教授。很可惜我沒有機會到現場去聽這場演講,不過從摘要來看,張教授是以原住民為基底的虛構小說,作為評論的方向(包括諸如《小矮人之謎》,《鰓人》或者《苦雨之地》等創作小說);甚至我們可以把前陣子以阿美族神譜作為劇本的電視劇《無神之地不下雨》也包含在這裡面。這也符合於我在前面所提到的四種原住民與AI的方向之一:作為原住民創作的評論與銜接之處。
這些和AI相遇的另一層文化關係,則來自原住民(在地)知識的應用轉換。這個部分可以稱為另一種AI(原民銜接,articulated indigeneity。也參見James Clifford在《復返》裡面的討論),不管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或者是articulated indigeneity,都是對於AI在原住民文化裡的另類關聯。我們可預見,有越來越多的AI,正在原住民的土地上生根發展,甚至長出新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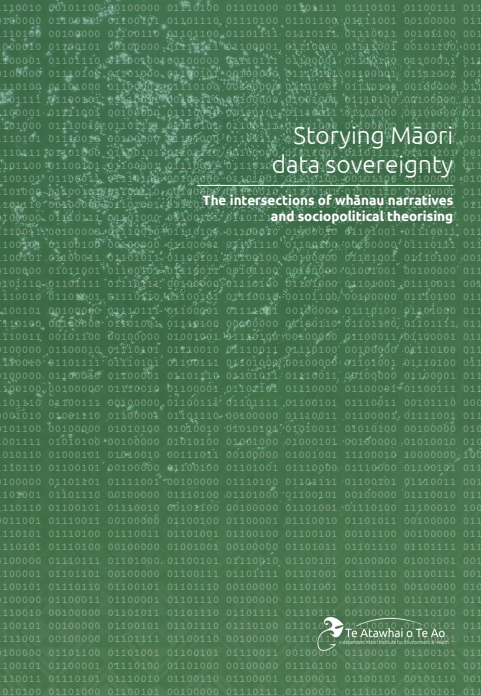
Kiri West, (Rawiri Tinirau ed.) 2023. Storying Maori and Data Sovereignty: The intersections of whanau narratives and sociopolitical theorizing.
歡迎進一步參考:
Salter, Chris and Alexandre Saunier. 2023. “Anthropology of the Artificial,” Visual Anthropology Review, 39(2): 448-456.
Kesserwan, Karina. 2018. “How can Indigenous Knowledge Shape our View of AI” Policy Opinion Politiques. https://policyoptions.irpp.org/magazines/february-2018/how-can-indigenous-knowledge-shape-our-view-of-ai/
Kukutai, Tahu, and John Taylor eds. 2016. Indigenous Data Sovereignty: Toward an Agenda. ANU press.
Kiri West, (Rawiri Tinirau ed.) 2023. Storying Maori and Data Sovereignty: The intersections of whanau narratives and sociopolitical theorizing. Aotearoa, Te Atawhai o Te Ao Charitable Trust.
網路資源:「人文社會課程之生成式AI指令集」種子範例: https://nthuhssai.site.nthu.edu.tw/p/404-1535-254188.php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馬上瘋檳榔 從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到AI(Articulated Indigeneity):如何在人工智慧裡與原住民族對話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7038 )



回應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On the data sovereignty part, Taiwan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a new EU-initiated standard on "international dataspaces" specifically focusing on data sovereignty and data sharing. It doesn't rely on any web3 or blockchain initiatives and become the tech foundation of EU Data Act, AI act and many others.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