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太陽花專家。這篇文章並不是要討論太陽花做為歷史事件的意義。我認識到的太陽花運動,是標記了台灣社會意識到未來將何去何從的歷史轉折過程,而我關心的是:在這此運動之後,台灣社會是否真的已經擺脫、超越現存經濟思維或資本主義邏輯,從而能對未來經濟生活及其體制進行基進(radical)想像?我將從幾個例子來呈現(後太陽花的經濟想像中)有關民族國家與新自由資本主義的關係。這篇文章唯一能做的事,是點出問題的複雜性,而不是提出最終解方,因為這是比單論資本主義體制的運作與後果更加艱難的課題。

我想,太陽花運動觸及了三個經濟人類學課題:第一,自由市場是拯救經濟疲軟衰退的唯一出路嗎?第二,資本是中性透明的數字的再現,或是一種關係?第三,在資本與統治階級聯手下,我們的未來,該何去何從?本文將聚焦在第三個課題,前兩項主題已經發表於芭樂人類學(一、二),在此僅簡述重點。第一,自由市場是經濟強國如英、美等自我證成的歷史神話,而自由市場的經濟模型是經濟學理論長期透過政治力量與學院知識生產體系相互為用,而共同形塑出人們別無選擇的理論幻影與霸權性格。第二、資本意味著社會關係,而跨國資本有其國籍(nationality),因而是一種政治經濟的複合體,其作用形式與方式必須放置在歷史社會脈絡中來檢視。任何將國際資本中性化、去政治化的論述與觀點,本身即是政治作為。弔詭的是,面臨中資時,我們很清楚資本做為一種關係的關鍵性,但面對其他國際資本時,則又強調其作為客觀再現的貨幣資本。然而,對於當代國際資本做為金融資本的意義,多數人仍無法清楚看穿,以至於資本流動總是被輕易地假定為經濟發展、成長的同義詞。
一直到頂新事件之後,資本家與統治階級聯手大玩金融遊戲、躲避監督以獲取暴利的劇碼,才進入正式進入我們的意識之中,並確認了過去對於資本與統治階級關係的猜想與拼湊。而金融資本受害者浮上檯面並得以具象化,更讓我們目睹掌握知識與裙帶關係的資本與統治階級,如何在極短時間內快速累積資本。從日常生活的細節中,抽絲剝繭梳理出拼湊出兩岸金融權貴緊密糾結共生的整體輪廓。首先,多年前因為油品安全事件無法在台灣立足生存的頂新,前往中國以泡麵創造高營收翻紅。在臺灣透過入股、轉投資台資集團與公司來接收他們在市場上既有的利基。取得主導權後,頂新內部不斷透過改變產品的製程、設備與原料來降低成本,並因其擁有許多知名品牌名氣而能獨占鰲頭。2008年ECFA簽訂之後,馬政府以貿易自由化、吸收外資與鮭魚返鄉作為訴求,這些政策乃是新自由主義對市場及資本進一步去管制以及將資本化為民族主義情感的表現的矛盾合體,提供頂新以名氣作為資本、以舊股換取市場資金、以遊走兩岸權貴為優先圈購TDR套利的對象,在台風光上市。

其中,執政者對民族主義情感的曖昧性,構成了頂新這類鮭魚返鄉「資本」的兩面性:表面上看似以投資台灣作為愛台灣的國族化資本,實際上卻是以金融手段來實現執政者心心念念的大中國國族主義情感,以及更綿密與更鞏固的跨境權貴政經聯盟。就此而言,國族主義及其情感象徵,並非資本自由化的對立,反而因為執政者與人民對於國族情感象徵的曖昧各有解讀,促成了資本的自由化,並繁衍了政--經--金三位一體的統治集團。
另一方面,衍生金融市場的出現與金融作為特許行業,皆是新自由主義的重要特徵,二者的出現與運作,必然是政治與經濟/資本共謀的後果:政治權力的繁衍需要資本的支援,而資本的繁衍與積累必須仰賴政權削弱自身的治理權限與範圍,才得以可能。在承平時期,這些全都被掩蓋、甚至有如政治無意識。由此,我們看到日常生活許多層面係為政經結構力量滲透,日常生活並非政治無意識的位址,一定程度上,日常生活可以成為揭露、甚至鬆動既有政經結構的阿基米德槓桿,正如個人自由不必然做為繁衍資本主義的所在。
這與太陽花和服貿有何關聯?一方面,了解服貿內幕的金融業者在太陽花期間已指出,在服貿中最大獲利者是台灣的金融業,而非其他部門。就此而言,服貿關乎金融資本自由化的程度。在新自由資本主義的重要特色,即是金融資本取代了貨幣而成為主流,金融商品的設計則是關乎利潤如何實現。而這些金融商品的運作,早已超乎一般人的知識視域,例如,衍生性金融商品與附買回的交易即是透過細緻的風險計算與重新組合,將不可能發生關聯的房地產抵押權當成利潤來源,而原本理應分散風險的金融商品,搖身變成由購買者與政府同承擔其高風險的惡果。更重要地,以新的資本形式出現在資本主義市場的趨勢,就是以短時間迅速累積超乎常人所能設想的鉅富,這是商品拜物教的極致表現。在當代情境下,資本積累與繁衍的邏輯除了萃取剩餘價值,最常見的反而是以尋租為手段或是以知識、技術與時間等,創新交易技法,使其擁有了不易被看穿的魔力。
另一方面,民族主義情感與民族國家界線的交錯、滑動,是跨海峽金融資本得以有效運作的文化形式。正是因為金融資本流動以民族國家與民族主義情感,服貿爭議才讓台灣社會意識到金融資本主義必然同時涉及統治階級與資本的共生結構。

在眾多尋找另類經濟可能之中,有機農業、社會企業與地方文化產業是目前多數人認為可以有效與新自由主義抗衡的經濟實踐,執政黨甚至將2014年訂為社會企業元年,準備挹注資金鼓勵。讓我以比較熟悉的地方文化產業為例來說明。文化產業是台灣政府用以促進地方產業與地方意識的手段,但是地方文化產業,或者說,引入原住民聚落的社會企業,必然面臨到以下問題:族群文化中那些層次與面向,可以被商品化而不引發社會道德爭議與利潤分配之爭?被商品化的文化形式、知識與意象既是族群整體所有,商品化意味著引入所有權的概念。只有在確立所有權的所有者之後,居民才能據此對利潤進行分配。
另一方面,在文化形式轉為商品的過程中,個人投注的創意究竟要如何被理解、看待?既有的社會階序關係在文化形式商品化的過程中,能否以傳統權威來宣稱其所有權,進而做為排除他人進用文化形式的合法基礎?最後,我們如何持平地看待文化商品在法律與傳統權威、個人創意與神話正當性、尋租與利潤分享等不同層次的倫理張力?這些問題在過去的研究中皆已討論,本文要聚焦於:當文化形式變成商品與資本之後,是否同時擁有了轉轍至商品拜物教的潛力,從而掩蓋了剩餘價值的萃取乃至於階級分化的問題?
如果文化產業是一種經濟活動,那麼,同一族群內的資本有無或財產有無,是否為實然?若為實然,我們才可能討論這類產業的形成、運作與後果。如果階級問題是文化產業中有關族群與資本關係之間的實然,那麼為何在類似個案研究中,階級問題仿佛穿上隱形斗篷、自動消失了?因為文化產業屬於族群事務,因此階級問題自動起身讓位?或者,以族群文化形式為商品的經濟實踐與場域中,剝削或者萃取剩餘價值根本不存在,就如同我們在許多以家庭關係為基礎的企業所做的分析個案中所觀察到的一樣?萃取剩餘價值與階級分化,究竟是實然上的不存在,或是研究者視而不見?換個角度來問:階級分化是否只存在漢人與漢人之間以及漢人與原住民之間,卻不存在於同聚落的原住民之間?若是如此,研究者該如何對原住民資本家與被雇用的原住民間的關係,加以定性?為什麼同一聚落的原住民之間,竟然存在著資本累積上的差異?
讓我們自問:過去四十年來,原住民社會是否從來不曾改變過,而只有我們這些生活在西部的漢人所身處的社會發生了劇烈的變動?如果說原住民社會歷經日本殖民以來的資本主義化與國家化而絲毫沒有產生任何改變,我們應該可以改寫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史的軌跡與邏輯。顯然不是,但要講出這個事實,何其困難,問題不在於我們欠缺界定階級關係的知識,而是研究者對地方社會與族群文化自主性,賦予許多應然的倫理意涵。或者,讓我來問個假設性的問題。當你要去奇美或鴻海集團應徵工作時,請問你是否會預期或希望,因為資本家與你屬於同一族群,出自同一族群身分的親近關係與道德性,在工作場所中給予更貼近人情義理的、非資本主義式的待遇?應該不會。我們很清楚,對奇美與鴻海而言,資本主義邏輯才是真正的掌權者。相較之下,我們會預期甚至希望在聚落/地方社會層次所發展出來文化產業/社會企業,能擺脫資本主義的邏輯,做為實現親屬/人與人之間的道德性,關懷文化傳承、促成社會永續發展。將族群文化產業視為道德經濟的實踐,是研究者與/或參與者的期許,至少,從我個人的觀察,當地人對聚落中同族群身分居民間的階級關係,感受更為敏銳,批判力道也更強。不願意正視地方社會文化產業中階級問題,不必然是當地人,很可能是研究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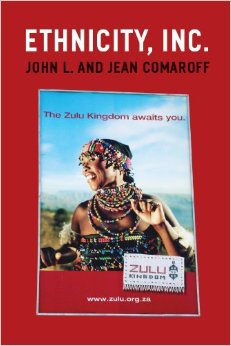
正如Comaroff夫婦在《Ethnicity Inc.》一書所言,以族群文化形式所發展出來產業或企業,既是政治經濟問題,也是倫理的問題。研究者不該只關注到所謂族群意識的政治表達問題,或是強調族群產業將如何允許弱勢者/邊陲者在市場帝國主義中被賦權。事實上,族群產業的運作,即是民族國家與新自由資本主義彼此有所關聯的微型宇宙,請容我大膽指稱:一個研究者看待與定性族群產業或地方文化產業或者原住民聚落的社會企業的視角,幾乎很難有別其看待民族國家與新自由資本主義的視角。當然,引入帝國主義壓迫與反壓迫的角度來討論這類問題時,也得留意這個層面在不同尺度會以不同形式出現,不能無故歷史社會實在而任意加以定性、批判。礙於個人學識有限,本文將集中在國家與經濟剝削這個層面。
事實上,有關民族國家與新自由資本主義間的張力,同樣以不同形式出現在我們如何思考是否還有另類經濟可能的烏托邦思想。以下我所要討論的烏托邦,不是小說1984、The Giver或者法國電影華氏451度那種強調純粹理性、崇尚合理化、全面監控、去除記憶、情感和性慾的那種藍圖式烏托邦。我想談的是與這種對反的、破除偶想崇拜的烏托邦,或者,反藍圖式烏托邦的烏托邦,意即,一種對於現存體制的基進思考、想像與希望,但不擘劃完美無缺的施工結構圖。
此一烏托邦想像必然為社會學家Erik Wright抨擊,他會認為這些看不到具體方向與命運的烏托邦想像,只會讓人們陷入無所適從的深淵。Erik Wright倡議我們應想像真實烏托邦,並以此做為改革體制的實作起點。與許多倡議相較,我認為Erik Wright對於目前各種另類可能的觀察,是相當準確的:社會民主試圖透過國家來馴化資本宣告失敗,而透過革命來瓦解資本主義亦不可行。而真實烏托邦,亦即,有清楚的方向與藍圖與制度設計,讓改革現存體制得以可能,更可免除各方勢力與想像角逐所帶來的內部衝突與能量耗損,在資本主義的縫隙中找到改革可能,進而侵蝕資本主義。事實上,他提出了改良後的烏托邦實踐綱領早已在許多地區實踐,例如社會經濟、工人合作社、社會資本主義或者社會市場經濟、社會企業、公平交易、有機小農產業鏈等各項社會創新,以及參與式預算。重要的,Erik Wright清楚意識到,這些真實烏托邦想像往往假定了民族國家的存在,從而容許人們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相較之下,工人合作社看似以階級為基礎,但是其運作範圍與可行性,依舊在民族國家界線。身為馬克思論者,Wright比任何人都清楚意識到這當中的緊張關係。
在這些烏托邦想像中,我感興趣的是一個早已被想像卻尚未真正實踐的基進經濟想像: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或Universal Basic Income(無條件基本收入)。這個烏托邦的制度設計很簡明:每個國家的國民從出生之後,無論貧富,均有權可以領取維持基本生活的收入。如此一來,工人若想行使罷工權時,可以不必因為養家活口的壓力而屈服於資本家,若資本家需要勞動力時則必須提供合理的薪資來留住勞動力。此一制度設計被認為能有效減緩階級之間的權力不平等。其次,當每個人想進入勞動力市場時,不再是迫於現實壓力,而是自願去工作,並能從工作中得到成就感。再者,因為每個人從搖籃到墳墓都有能夠維持基本生計的收入,甚至連家務勞動者與重病照顧者,不再因為親屬道德性而必須全年無休的無償照顧重病者。弔詭地是,目前由福利體系所提供的各種福利救助,如健保、失業救濟、兒童津貼乃至喪葬津貼等,皆可取消,交由市場提供。如此勢必削減國家權力,而政府的經濟功能即是將稅收進行再分配,並且使稅收基準的設定更加完備,確實執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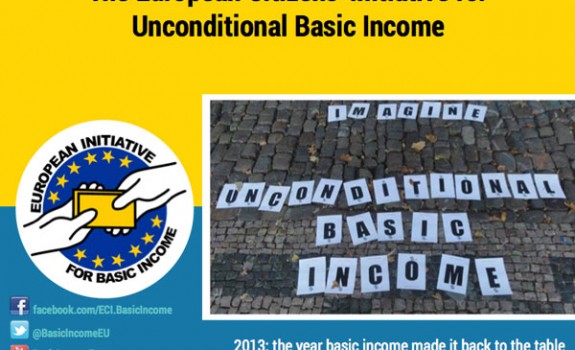
此一烏托邦想像的人類學蘊義(implications)為何?
首先,這個想像衝擊到資本主義以及一般人對於人與勞動的基本預設:人必須勞動來換取生活所需,無論那是工資或食物。如果有人領取基本收入後,天天遊山玩水逍遙度日,一般人很難接受自己勞動所得是如此被運用。換言之,無條件基本所得這個烏托邦想像,觸及了我們對經濟生活的倫理核心:勞動使人得以維繫生命並進行社會繁衍,以及勞動所得/工資只能為個人與家人所用的私有財產權觀念。
無條件基本工資直接挑戰了我們對於人做為勞動者與工作的界定。試問,藝術家的創作可算是勞動嗎?參與社會運動、從事改革可算是工作嗎?這些人對社會是否有所貢獻?若有,為什麼人們注定餓著肚子去從事這些工作?相較之下,其他人似乎平白無故享受了這些人的工作成果,但他們似乎並未從這些投入與努力中,獲得應有的回報。或許你會爭辯,這些工作就是因為沒有物質回報,才顯得高貴。然而,若有才華的人遲遲得不到應有的回報,被迫須放棄藝術甚至生命,那社會豈不是扼殺了一個藝術靈魂,來成就社會集體所稱許的高貴情操與美德?更何況,無條件基本收入制度設計,是從個人對社會集體的貢獻來重新思考何謂工作這個根本問題,同時是以大企業的資本利得為主要標的來實現分配正義。
基本無條件收入這個想像,對習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人所造成的強烈衝擊在於:資本主義以生產為導向的意識形態,蘊含了將人原子化,孤立其存在,更窄化了人做為勞動者、勞動、與成果分配等的看法。在此意義下,無條件基本收入不只是對目前經濟思維的基進想像(radical imagination),更是倫理想像(ethical imagination):行動者要考量自我與他人以及自我與世界等層次的存有樣態,再來思忖應該採取的行動與實踐。弔詭的是,這個烏托邦想像卻很可能造成國家的弱化、個人更加原子化與孤立的後果,使市場成為主導我們生老病死各項社會服務的機制,加深我們對市場的依賴。一方面,我們有挪用商品與服務的實踐,使其能為人所用、實踐以人為本的經濟,透過不同主體位置的來實踐前述倫理想像,使自身得以主體化。另一方面,削弱國家權力並不必然是壞事,若能鬆動統治階級與資本相互為用的共生結構,再好不過。
當代情境下的倫理想像所勾繪的存有樣態與經濟生活,是否與Polanyi提議之受社會規約的市場若合符節?的確,最近十多年來,社會學與人類學界在處理新自由主義所造成經濟後果時,有志一同地訴諸Polanyi的論點,以此做為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的出路。就此而言,Polanyi對於市場應受社會規約的論點,同樣假設了民族國家的存在,儘管贊同其論點的學者對於「社會」指涉為何,各有想法。換言之,Polanyi的論點依然假定民族國家具備有效治理資本自由流動的能力。若我們將此假定放回Polanyi當初寫作The Great Transformation的時代脈絡,是合情合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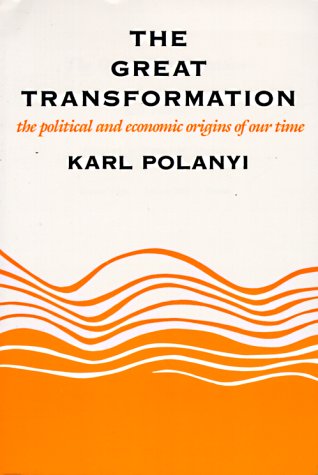
另一方面,從「社會」出發討論未來經濟的可能出路,必然蘊含了可實踐的社會道德性。請容我更基進地提問:此一社會經濟圖像,如何安置個人做為經濟主體的想像與未來經濟圖像呢?很明顯地,個人對未來的想像與希望就只能被含括在整體化的社會想像與社會希望之中,那些溢出於社會想像之外個人想像與希望,將很難再被看到。在太陽花運動中,我觀察到的個人做為經濟主體,是在特定主體位置與多重關係性之中的人,而不單單只是新自由資本主義下那種個人主義式的個人。對我而言,從個人的倫理想像所牽連的主體位置、多重關係性與多重存有樣態,來重新省思未來經濟的圖像,並非不具備社會性。相反地,在一個人對未來經濟進行倫理想像時,即意味其將他者與世界的關係性納入想像的視域。在太陽花運動這類歷史轉折過程中,人們對未來的希望與想像,必為其行動與實踐提供養分。我認為,這些已出現或者即將正在出現想像與希望是促成人們能動的驅力,而那些看似個人化的未來意象,將會成為那些尚未到來(not-yet)之未來與希望的行動觸媒。
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在那些未來的經濟想像與經濟體制的重構中,重新打造能夠馴化資本的民族國家,不僅是被假定的存在,更成為未來意象的終極目標,是做為我們與新自由資本主義抗衡的碉堡。對於厭惡也厭倦了國家資本流動的人而言,重新賦權民族國家是最立即、最清楚也最有可能的作為。類似想法同樣出現在後金融海嘯的美國社會中,被資本流動所穿透、擊碎的民族國家界線,被想像成危及國土安全的侵略,因而有重新修補、強化的急迫性。
其實,我們無法想像一個沒有國家的社會,更無法想像沒有國家主導的經濟。寫這句話並不是對誰進行批判,反而是要去問:為什麼我們無法如此想像呢?當我們在講述打造民族國做為一種未來的歷史必然時,我們究竟意味著什麼?我們當然意識到目前民族國家與資本流動相濡以沫的共生結構,為何認為強化國家主權對於經濟主權的治理時,是一個依然可行、有效的政治作為?就這點而言,我相當程度會同意David Graeber所倡議的,因為認識到這些問題在結構上的癥結所在,因為意識到代議民主與資本的相互支撐,因而只能砍掉重練,一切重新來過。
這是烏托邦,你一定這麼說。
是啊,我從來沒否認過。
生活在這塊土地上,我非常清楚提議打造新國家以抗衡新自由主義的資本流動,實際上牽動了多少人內心深處的歷史情感、傷痛與渴望,甚至有著全然奉獻心力那種近似神聖的革命熱情。正因為認識及此,我才更要提問:當我們將打造(新)民族國家/以族群身分為基礎的地方社會,視為對抗新自由資本主義侵蝕的可能性時,我們要如何避免已然存在的人群快速流動的異質混雜社會?當我們強調從一個整體化的社會觀即能思考出未來經濟出路與實作時,將如何面對個人做為社會行動與想像之基礎的當代處境?
你說,何苦提這些無法立即有效解決現狀的問題?這只是徒然將問題複雜化。
我想說,如果對未來進行基進想像的能力與勇氣都沒有的時候,我們又將變成什麼模樣?
寧靜的夜半時分,我不禁這麼想:是否民族國家之於新自由資本主義,有如愛情之於貨幣?
我無意輕佻。只是希望透過不同思考路徑與象限,刺激出有別於當下、甚至與當下具有革命性斷裂的基進想像。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鄭瑋寧 民族國家之於新自由資本主義,有如愛情之於貨幣?: 我所知太陽花的二、三事(318週年系列5之4)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426 )



回應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非常激賞作者由人類學高度思索經濟模式的基進可能性,但目前看到一點疑義,提出商榷:UBI應該不會加深人們對市場的依賴,原本被工作體制綑綁住的勞動力釋放出來之後,很多原本必須要透過市場解決的問題(比方長照、托幼)都可以回歸社群之間的互助經濟,讓人們不必透過市場的金錢交易來滿足這些需求。
另外有一點補充:各種產業的自動化趨勢,會讓UBI的世界顯得更有可行性,甚至應該說,讓UBI的世界更有迫切的必要性。如果不透過類似UBI的顛覆性重分配來重新定義工作、定義經濟,人類勞工就會在各種自動化機械和人工智能的威脅下,顯得越來越缺乏就業能力,同時也就意味著被市場經濟淘汰掉,被宣告為沒有資格活下去的人。相反地,透過UBI的顛覆性重分配,原本由資本階級所壟斷著,那種種自動化器具和專利技術,就變成為所有人的基本生存服務,而不只是為了少數資本階級的利益服務。
最後附上拙作: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5%A5%89%E5%90%9B%E5%B1%B1/%E5%8F%8D%E6…
以及最近跟朋友討論「工作」的倫理學意義的討論串:
https://www.facebook.com/jyunshan.fong/posts/10153206585747658
"基本無條件收入"不一定要由政府提供。在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 (中譯物聯網革命)一書提到了自造者的興起,當科技條件滿足少量多元的需求時,以社區為單位自求溫飽的可能愈來愈高。反過來說,若公平正義重分配事事要求助政府,多元社群文化豈不更遙不可及?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