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像在哪裡看過這齣
人類學家評《全員在逃》
今年五月剛由衛城出版的《全員在逃:一部關於美國黑人城市逃亡生活的民族誌》在台灣宣傳的策略非常明確:儘管有著非常高的評價,這本書同時也極具爭議性。甚至隨著此書的出版,在網路上唯一相關的中文文章是一篇由一群學生寫給作者社會學家愛麗絲‧高夫曼的公開抗議信的翻譯。至於爭議為何,中文版的導讀已經談得很清楚,我在本文稍後也會補充。而身為一位人類學家,看到隔壁棚社會學界的紛擾,不禁想起自己學科過去幾次類似的內戰,例如80年代「民族誌再現了什麼樣的事實」的書寫文化反省浪潮、90年代中「人類學家是客觀科學家還是有道德責任的社會工作者」的辯論、90年代末「西方白人學者真的懂邊緣族群在想什麼嗎」的三百回合大戰等等。其中,我覺得與《全員在逃》爭議最相似的,莫過於美國知名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於1928年出版的《薩摩亞人的成年》之後所掀起的爭辯。兩本民族誌都是系出名門的年輕學者的初試啼聲之作、其資料都來自二十出頭的年紀時所開啟的田野工作。兩本書都奠定了作者在學科內的地位,也都有為大眾書寫的企圖,而之後面臨的批評也都牽涉到報導人敘事的真實性與對異民族文化描寫的公正性的問題。最後,兩本書的附錄其實才是作者真正研究精神的所在,而對於附錄的重新探索與比較,可以讓我們在一片爭議聲中為兩者辯護。

米德與薩摩亞姑娘們
1925年八月,才剛進入由美國人類學之父鮑亞士主導的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博士班兩年、且新婚不久的米德,隻身抵達了美屬薩摩亞,即將展開她為期八個月以島上青少年生活為主題的首次田野工作。返國後,她完成了《薩摩亞人的成年》一書,其論點為有別於美國青少年,特別是女性,在青春期面臨各種心理與身理變化的騷動不安,對薩摩亞青少女而言青春期反而不是一段艱困的轉折時期。她們不但剛從照顧弟弟妹妹的家務責任中解脫出來,而捕魚、搜尋食物和編織等新的任務也給予她們充分的機會與男孩子互動、談情說愛,甚至體驗性行為。青春期因此是她們最終嫁為人婦前最自由愉快的時光。也就是說,青春期並非普世皆然的生物成長階段,而在不同的社會文化中會有不同的樣貌。
《薩摩亞人的成年》鮮明的社會評論色彩在出版之後很快地得到美國評論家的青睞,但其挑動保守社會敏感神經的性行為描述,則引起一些負面回饋。在學界內一開始的高評價(包括田野工作祖師爺馬林諾斯基),也逐漸轉向為對書中過多普遍性的陳述的批評。儘管如此,這本書還是獲得商業上高度的成功,也讓原本被視為禁忌的女性私密經驗得以被公開討論,更樹立了一個公共人類學的典範。然而在米德逝世的四年多後,紐西蘭人類學家德瑞克‧費里曼(Derek Freeman)根據自己於1940年代在薩摩亞生活經驗以及隨後多年的檔案與田野研究,於1983年出版了《米德與薩摩亞》(Margaret Mead and Samoa: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an Anthropological Myth)一書對《薩摩亞人的成年》進行嚴厲的挑戰。他的批評不似之前學界內外關於道德立場與資料陳述的評點,而是近乎人身攻擊地推翻米德在薩摩亞的研究。他的論點主要是青春期依然是一個普同的生物階段,充滿生理心理上的轉變與衝突,在薩摩亞的階序社會中更是如此,因此米德所描寫的自由體驗性行為的狀況是不可能存在的。而她之所以會寫下這樣的結論,不僅是因為粗糙的田野工作與鮑亞士「文化決定論」的成見,更是因為她天真地聽信薩摩亞姑娘對她撒的漫天謊言。費里曼也讓原本對《薩摩亞人的成年》的書寫方式就有些不滿的當地聲音充分表露。許多薩摩亞人認為書中對薩摩亞人性生活幾乎獵奇式的描寫,不但與事實天差地遠,也否定了他們身為人的價值。
米德與費里曼的辯論是人類學史上的著名公案,其相關討論多不勝數,礙於篇幅在此只能扼要論之。簡單來說,費里曼的研究來自男性觀點、時代不同、位於獨立薩摩亞的田野地與美屬薩摩亞也有歷史發展上的差異,因此其挑戰有如張飛打岳飛。他對米德書中與檔案中的資料也多選擇對自己有利的部分分析。最後,被他指認出來誤導米德並曾在一部紀錄片上公開自陳的薩摩亞姑娘(此時已是八十幾歲的老嫗),也可以從米德田野筆記中發現非但不是主要報導人,在書中甚至只出現在一段中(也就是中文版頁40的帕娜)。事實上,米德非常清楚謊言玩笑存在的可能性,其材料來源也相當廣泛,不是只依賴一兩位報導人的片面之詞。最後,她並非極端的文化決定論者,在書中也認可青春期作為一種生物發展階段的存在,只是會在不同的環境中受不同的元素影響。
《薩摩亞人的成年》的定位其實一開始就是寫給大眾的「輕學術」作品,而米德想要傳達給美國讀者關於青少年發展、教育、女性意識的訊息也確實使她在薩摩亞資料上進行過度的詮釋。但她還是有基於薩摩亞田野的嚴謹學術著作,也就是《瑪努亞島上的社會組織》(Social Organization of Manu'a),還有博士論文《玻里尼西亞文化穩定性問題之探索》( An Inquiry into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Stability in Polynesia)。這些能反映她紮實的理論和方法論訓練的面向,則是展露在《薩摩亞人的成年》的附錄中(很可惜地中文版沒有翻譯出來)。裡面她提供了完整的研究設計、25位青春期少女的量性資料、對薩摩亞文化受到傳教士與殖民的影響也有清楚的掌握。這個附錄與日後被收入檔案中的田野筆記,成為在她過世後能為她持續辯白的最佳武器。然而,對於將這些資料毫不加修飾地呈現而對薩摩亞人造成的傷害,米德生前是相當懊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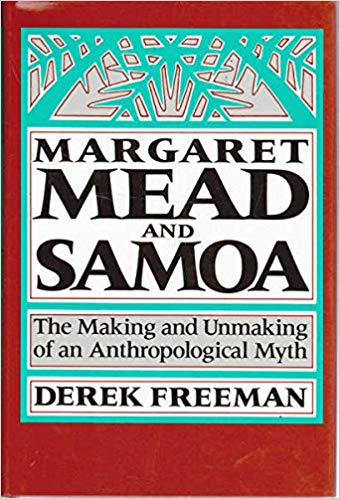
高夫曼與六街男孩
2003年一月,就讀賓州大學的高夫曼首次與日後她將寫進《全員在逃》中的南費城六街男孩相識。這些男孩可不是一般的鄰家少年:他們多半參與幫派犯罪活動、蹲過感化院或監獄、有案底在身、甚至處於假釋或被通緝的狀態。在拘留所、法庭之間來回遊走、在警方的監控與騷擾下設法逃脫是生命的常態。隨著她與這些男孩及其親友的關係越來越緊密,這個一開始是想瞭解都市邊緣黑人社區生活的大學課堂報告,逐步發展成大學畢業論文,以及她在普林斯頓社會學系的博士論文,最後則改寫成2014出版的《全員在逃》。用高夫曼自己的話來說,「本書將說明[年輕黑人]監禁人數的快速成長,以及更隱匿的警方監控行為,描述生活在費城相對貧窮的黑人社區的年輕人的經歷且瞭解他們。」(頁34)另一方面,「即便在警方攔檢與緩刑報到之間遊走不定,當地居民仍在為自己開創有意義的生活。懲罰與監控的範圍無法阻止他們建立一個能得到尊嚴與榮譽的道德世界;年輕男女在警方的天羅地網中,掙扎著工作、家庭、愛情與友情。」(頁44)
與《薩摩亞人的成年》相似地,《全員在逃》在出版之初立即獲得學界內外近乎一致的好評,甚至得到傑出黑人學者康乃爾‧韋斯特(Cornell West)和以利亞‧安德森(Elijah Anderson)的背書。類似的主題在都市社會學的研究中不是沒有被探討過,但高夫曼的材料是如此地綿密透徹、且能夠深入各種大小或私密或公眾的空間中,論者認為若非紮實的田野工作是蒐集不到這樣的資料的。書中關於這些在警方監控下的黑人青少年的女性親友如何應對這種狀況的觀點,更是在之前的研究中少見的。
若要說在《全員在逃》的評論中有一個像費里曼之於《薩摩亞人的成年》的角色,那這個人就是西北大學的法學教授史蒂文‧盧貝(Steven Lubet)。有別於一開始一些基於資料呈現手法與高夫曼白人菁英身份的批評,盧貝在一篇2015年的書評中認為《全員在逃》裡多處出現依他過去擔任青少年與刑事辯護律師的經驗是不可能發生的法律事件,並質疑高夫曼的田野工作並非多數論者認為的那般優秀,而是根基在許多未經查證的街坊謠言上。他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剛滿十一歲的提姆因為坐在哥哥開的贓車上被逮捕判三年緩刑的判決(頁50),另一個是警方進入醫院中翻閱訪客名單追捕通緝犯的手法(頁80-81)。他與相關人士求證的結果是,這兩個案例都是極度不可能出現的狀況,就算有也不是常態,但在高夫曼的筆調下卻像鐵一般的事實。這個書評觸發盧貝在今年出版了《審問民族誌》(Interrogating Ethnography)一書,裡面分析了五十幾本他能夠針對細節求證的美國都市民族誌,並發現大部分的民族誌作者都缺乏「事實審查」(fact check)的動作或聲明(戴斯蒙的《下一個家在何方》是少數例外),並經常輕信報導人的敘事然後順理成章地書寫出來。更麻煩的是,他們可以更改細節來保護當事人與田野地。雖然這些大大小小的故事多半不影響整本書的論證,而有些作者也能依靠修辭如「據某某人說」來潤飾,但他認為這並非一個理想的社會科學的研究方式。
在盧貝開了這槍後,高夫曼突然從社會學界的耀眼新星成為眾矢之的,學界內外從不同角度重新檢視《全員在逃》的負評紛紛出現。有人發現更多前後矛盾不合常理之處、有人指控她造假或誇大社區的陰暗面、有人覺得她的研究從來沒有真正得到六街社區的知情同意、有人指出全書多次出現的量性統計資料有嚴重的瑕疵、有更多少數族裔學者和學生則認為這又是另一本白人研究者踩在邊緣社群身體上進入學術殿堂的作品,而處於尊貴的賓州大學旁的南費城黑人社區更時常是任其學生進出的後花園或實驗室。最後,甚至還出現了一封匿名投訴信,嚴重到高夫曼任教的威斯康辛社會學系得對她進行是否違反研究倫理的調查(最後結果公布為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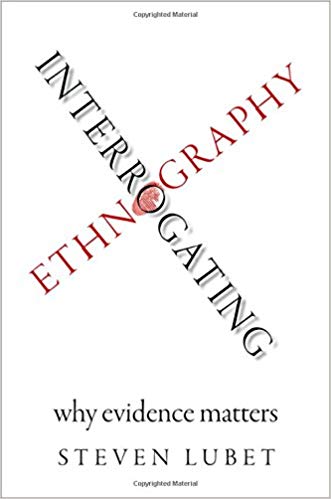
為《全員在逃》辯護
若與《薩摩亞人的成年》做對比,可以發現對兩者的批評在本質上十分相似,大體而言可以分成(一)資料真實性的問題(無論來自被欺騙、輕信、誇大還是造假)以及(二)書寫他者的公正性(薩摩亞少女的性生活、六街男孩的犯罪人生)。上面已經提過,米德的附錄資料以及田野筆記檔案得以幫助她洗刷關於第一點的冤屈。例如附錄表格中25位薩摩亞少女異性性行為經驗與她們距離初經的時間長短是相關的,也就是說若她們是在隨機撒謊,那麼這個數據應該會呈現較混亂的分布。然而高夫曼沒有辦法這麼做,因為她為了保護當事人,已經將所有的田野筆記銷毀,甚至封鎖了其博士論文的線上資訊。而書中許多人物日期上的矛盾,她則表示是基於同樣的理由更動的結果。
然而高夫曼的長篇附錄〈方法論的筆記〉反而能幫助她回應米德最無能為力面對的第二點質疑。在這個附錄中,她從自己如何進入第六街社區開始談起,並且如何一步步與六街男孩們建立在外人眼中十分不尋常的關係,同時摸索自己在其中的位置。中間她提到了自己與那邊天差地遠的優渥出生和資源,最後則以好友查克遭槍擊身亡的故事收尾,以及這個事件如何撼動她身為研究者的角色。如此赤裸裸的自我剖析,在許多批評者眼中反而更坐實了那「她只在乎自己」的指控,而她提到自己載著手持手槍的邁克一同驅車尋找殺害查克的仇人的情節,也被盧貝指出有觸犯賓州串謀謀殺罪之嫌。
我反而認為在這個人類學界泛稱為「反身性」(reflexive)陳述的文體中,高夫曼毫不避諱地展現了在這個研究中早已沒有中立的客觀性,但也表明在這樣的狀況下研究還是可以進行下去。她與六街男孩及其親友的情誼、她的深陷其中,讓她看到了這個社區最黑暗的一面。也是基於這樣的情誼和瞭解,她可以在邁克五年內至少出庭受審的51次中,出席其中的47次(頁58)。這已經不只是田野技藝而已了,而是一種對朋友的忠誠。我認為許多針對《全員在逃》的批評固然有其道理、我能理解那些少數族裔學者和學生的不滿,但這其中也隱含著一種妳這白人女性憑什麼能瞭解這群黑人少年、憑什麼能與他們結為好友的有罪推定和雙重標準。在台灣早先翻譯出版的《我當黑幫老大的一天》中,作者印度裔社會學家蘇西耶‧凡卡德希違反的研究倫理恐怕更多也更明顯,但也沒有面臨到像高夫曼現在幾乎人人喊打的狀況,在台灣的宣傳也沒有針對其爭議性在做文章。為什麼?只因為凡卡德希是棕色皮膚嗎?有意思的是,最後反倒是一位記者基於「事實審查」精神的報導,能夠為高夫曼平反。這名記者拼湊出第六街的所在地,拿著高夫曼的相片到處向人打聽,最後竟找出查克的母親並坐下來與她進行訪談。期待她會揭露高夫曼的真面目、或像薩摩亞人那般表達對《薩摩亞人的成年》的不屑的人恐怕要失望了。查克媽媽如是說:
她是所有人的好朋友。她與我的孩子們和其他男孩建立了深厚的關係,成為非常緊密的朋友。我甚至還見過她的爸媽(註:高夫曼知名的社會學家父親厄文‧高夫曼在她出生那年已過世,這裡指的是她的繼父)。她會陪我一起出庭,非常地支持我。
問到對於《全員在逃》有何感想,她表示她還沒有看完,但完全相信高夫曼忠實地呈現了第六街的故事:
她說她看到的事情,那些在這裡四周的暴力事件,她說的是真的。查克死的時候她在他身邊、另外位男孩死的時候她也在、我的另一個孩子瑞吉被關的時候她在一旁、我小兒子堤姆被關的時候她給予充分的支持。她在這些所有事情中一路支持我。一路支持!所以,我真的愛她。
毫無疑問地,對一個民族誌工作者來說,這一番話的價值遠勝於任何正面的書評或學術引用,也遠超過任何關於何謂「民族誌事實」的爭辯。
對翻譯的建議
最後,我想稱讚一下《全員在逃》的翻譯。那麼多黑話俚語,真是難為譯者了。儘管如此,如果沒有在聽饒舌歌,有些地方還是免不了會翻得不到位,例如頁232「他有小大人(Biggie Smalls)的沈重鼻音」,正確翻法應該是「饒舌歌手聲名狼藉先生」。頁209『他們只會要求「婊子」(hood rats)偷偷拿毒品到會客室』基本上沒有問題,但hood rats特指為了利益什麼都願意做、水性楊花的女性社區成員,因此「地方上的破麻」似乎是比較符合的翻譯。類似的狀況出現在高夫曼特別處理的rider這種身份上,在書中直翻成「騎士」,但只要有聽過諸多關於rider的饒舌歌就會知道,這是一種共患難、豁出去的精神,與騎上去的動作無關。若要我翻,應該會是「相挺之人」,也會與頁114的翻法相符。還有,頁369『像是他們坐牢時讀的「俠盜」(hood)小說』應該是「街頭」或「貧民窟小說」。可能是因為書中太多俚語讓譯者開始草木皆兵,頁193「那些混蛋(Ant)」的Ant不是什麼黑話,而是書中一位角色Anthony的暱稱,翻成「小安」即可。最後,我對書中「黑鬼」的直譯感到有些不安,雖然出現的情境都是六街男孩彼此的稱呼,但這畢竟還是一個尖銳敏感的字眼。當然不用像《平凡的邪惡》的譯者將「猶太」翻成政治正確的「尤太」,但有些地方翻成「老兄」、「兄弟」,意思會比較貼切、也不會造成無謂的爭議。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林浩立 我好像在哪裡看過這齣:人類學家評《全員在逃》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670 )



回應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我最近剛讀完了這本書,然後外加啃了一點蘇西耶.凡卡德希的《地下紐約:一個社會學家的性、毒品、底層生活觀察記》,我發覺林浩立老師您的確指出了一個很核心的問題:「為什麼高夫曼在被罵得這麼慘,凡卡德希卻沒被罵?」
同樣是英文維基,高夫曼底下被列了一大串學術爭議,凡卡德希什麼都沒有。不僅如此就像老師指出的,在中文世界只看得到高夫曼的爭議,甚至在論述高夫曼的爭議時,都沒有看到講述者指出《我當黑幫老大的一天》與《地下紐約》這兩本比《全員在逃》早期且可能更具爭議性的。
我自己在看《地下紐約》時就感覺不對勁,如果說《全員在逃》的問題是題材選取、書寫視角與研究倫理,那《地下紐約》豈不比《全員在逃》還要更有問題?也許真的就像林老師您這篇文隱含的東西一樣,問題核心恐怕都不是書的本身。
謝謝回饋,對於凡卡德希的爭議還是有的(如這篇紐約時報的報導:https://www.nytimes.com/2012/12/02/nyregion/sudhir-venkatesh-columbias-…),但跟高夫曼比起來真的少非常多,攻擊力道也不同。我認為毫無疑問地與他們的「種族」、性別身份有關。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