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的平權之夢
論雷薩.阿斯蘭的《伊斯蘭大歷史》
美國最出名的穆斯林公共知識分子
雷薩.阿斯蘭(Reza Aslan)在美國是一位家喻戶曉的人物。或許再沒有一位當代美國穆斯林知識分子,如阿斯蘭這般受到媒體矚目。在二○一七年他透過推特批評總統川普的言論而引發爭議以前,阿斯蘭為CNN電視臺一靈性旅遊節目Believer製作團隊工作。平常,他的身影也可見於政治光譜極為不同的電視臺:從PBS到共和黨電視臺FOX,從反共和黨的Daily Show與The Colbert Report等一線的娛樂政論節目,一路到極端無神論且視宗教為垃圾的節目主持人Bill Maher的脫口秀。有人說他的外形英俊、風度大方、辯才無礙,使得他聲名大噪。那麼,這樣一個曝光率如此高的知識分子,寫出來的歷史書,究竟是一本什麼樣的書呢?

相信與不相信的人們都有福了,因為《伊斯蘭大歷史》是一本精采可期又深入淺出的伊斯蘭簡史。阿斯蘭說故事的功力是一流的。除了對於史料的熟悉,他在重構歷史時總是夾敘夾議,其批判總是詼諧,因此這絕對不是一本枯燥乏味的史書。阿斯蘭採取的敘事模式,是他最擅長的將史料考證變成精采故事的模式。畢竟,阿斯蘭另一本暢銷作,就是描寫耶穌的生平。同樣透過歷史考察、宗教研究的觀點,他清楚勾勒出這位拿撒勒人先知與後世基督教誕生的生動圖像,並深刻地提出跨宗教的人性關懷等問題。事實上,他的作品,總是與今日民主、人權、恐伊斯蘭(Islamophobia)與宗教容忍(religious tolerance)等當代議題緊密扣連。值得一提的是,阿斯蘭本人曾經改信過基督教,但在研讀宗教史後又重回伊斯蘭教的懷抱。出生於伊朗德黑蘭,但七歲以後都在美國長大並接受教育的他,有著什葉派家族的背景,不只鑽研過耶穌生平,對伊斯蘭有深刻的研究,同時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美國公共知識分子。這樣的一個人,其思考的寬度與言談的模式,足以成為在不同生活世界之人的橋梁。
宗教是社會的,也是文化交流的開花結果
那麼,若以具體的例子來說明,這大概會是一本什麼樣的書?我們該如何定位它?我可以幫助讀者的部分,或許是先提示這本書所使用的研究取徑,以供有興趣的讀者參考。畢竟,這不是一般的學術論文,而是一種人文社會科普書。在這樣的書中,一位學者的的研究方法不會一五一十排排坐好地列出來讓讀者知道。
讀者必須知道的首要之事,是這本書帶有強烈的重視意義詮釋的精神(意義是無比神聖的真實,而不在乎物理性質的真實),也表現出宗教研究中重視歷史脈絡與特定情境的解讀。從這樣的角度來看,這本書並非一般的神學科普書,而是一本研究伊斯蘭史的社會科學科普書。同時,這部作品也致力於顛覆一般大眾對於「宗教」在今日世界的角色之想像。在提到「一種常見但錯誤的想法」時,阿斯蘭主張我們必須破除那種誤以為「宗教是在某種文化真空中誕生」的想法,因為「所有的宗教都跟它們興起與發展時的社會、精神與文化背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這對於宗教人類學者或社會學者而言,當然不是什麼新的觀點,而是基本的學術知識。人類學者Talal Asad就曾經清楚地論證,現代世界所通行的「宗教」的觀念,本質上就是歷史的產物,而且是因為西歐的特定政治背景才產生,尤其是在西歐君主與中產階級試圖削弱教會勢力,將教會趕出公共領域,使得基督教再也無法提供公共秩序的解釋力之後,宗教別無其他領域發展,才轉向注重強調個人內心世界,構成注重心理層次的「信仰」。事實上,即使是不同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也時常陷入這種將「信仰」永恆化、視為是宗教本質的預設之中,但這其實是誤將基督新教在西歐的發展挪用為一種普世性的、橫跨時間空間的所有宗教實踐的單一標竿,並無法說明更為儀式性的、社群性質的、乃至群體行為規範與規訓的宗教形式在不同時代中的意義。
阿斯蘭的寫作方式的優點,是在於略過這些困難的學術討論,而直接用平白的話語來去自然化(de-naturalize)那些誤以為宗教只是某個先知突然領悟什麼而憑空發明出來的「信仰」的觀念。阿斯蘭與許多宗教人類學者及宗教社會學者的基本態度都是一致的:宗教是建立於人類社會之中的力量,並非自外於社會的東西,更絕非「信仰」這種將宗教力量內在化、心理化的觀念可清楚說明。在本書的前半部中,阿斯蘭就清楚地解答了,究竟穆罕默德是為了改變什麼樣的社會而慢慢建立起伊斯蘭的社群?先知周遭的部族政治、宗教與經濟、性別與權力又如何是他急欲改革的對象?阿斯蘭用許多史料證明了,伊斯蘭的發跡與發展,時時刻刻都與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息息相關,因此伊斯蘭本質上是一場又一場積極想要改變世態的精神與物質改革。

By Larry D. Moore, CC BY-SA 3.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29628662
如果在研究方法與思考路徑上,這本書是屬於宗教人類學與宗教社會學的,那麼,在寫作風格上,本書卻又採取了一種科普歷史說書的方式,而特別適合各種讀者來閱讀。由於阿斯蘭熟知阿拉伯文學詩歌以及中東廣大地區多神信仰中不同社群與不同神明之間的關係,因此,他除了將伊斯蘭的精神扣緊當時的社會文化脈絡之外,更掌握了《古蘭經》不同章節在先知穆罕默德生存的不同時期對同樣事件截然不同的回應。這樣切入《古蘭經》的優點,在於阿斯蘭可以證據充足而清楚地說明,究竟是哪一種社會結構與社會亂象,促使穆罕默德試圖透過伊斯蘭為當時階級嚴明的社會帶來激進的平權夢想。可以說,阿斯蘭忠實地將《古蘭經》還原為先知、社會、文化與神不斷互動的一本活的、充滿生命力的、蘊含瑰麗文學能量的口述經典。更難能可貴的是,阿斯蘭把當時的中東地區的宗教思潮背景,用極為淺白的方式,說明了伊斯蘭、猶太教與基督教是如何彼此借鑑、積極影響而繁榮共生(或延續保守)的模式。畢竟《古蘭經》承認所有的猶太教先知,也承認耶穌為重要先知,耶穌之母則是具有高超德性的女性,更不必說《古蘭經》有許多的人物與故事都與《舊約聖經》一脈相承。《古蘭經》受到猶太教詮釋經典的視角影響之深,可以從《古蘭經》原本並無「是夏娃先被蛇勾引」(原本是連同亞當一起)但卻被後世的穆斯林學者如此釋經解讀。除此之外,《舊約聖經》「命定的先知」之文學主題也時常進入到穆罕默德的傳說中,穆罕默德年少跟隨沙漠商隊時就有獨雲為其遮住烈日等意象,就是延續著先知撒母耳從耶西一家最小的兒子大衛身上看見了未來的王這種「小人物出頭天」的情節。
這些跨宗教神蹟故事情節之間的雷同並非巧合,而是多元文化彼此融會貫通的結果。這樣在歷史中存在悠久的模式,是阿斯蘭在本書開頭提及當代所謂的「一神信仰衝突」時,他真正要給予讀者的訊息:我們誤以為是一個個封閉的宗教,彼此之間其實從誕生前後都不斷交互著影響。
事實上,根據阿斯蘭對多種史料的考證,穆罕默德自己就曾經承認,他的訊息是想改革前伊斯蘭時期阿拉伯既有的宗教信仰與文化習俗,好讓阿拉伯民族認識猶太人和基督徒的神。《古蘭經》(42:13)清楚地說道:「〔神〕已為你們〔阿拉伯人〕制定正教,就是祂所命令努哈(諾亞)的、祂所啟示你的、祂命令易卜拉欣(亞伯拉罕)、穆薩(摩西)和爾撒(耶穌)所制定的宗教。」從這個角度來說,先知穆罕默德深信,猶太教、教督教、伊斯蘭是一脈相承、彼此聯繫的亞伯拉罕一神宗教。
那麼,為什麼穆罕默德要這麼做呢?他想改革的前伊斯蘭時期的阿拉伯社會,究竟是什麼樣子的呢?
穆罕默德:阿拉伯社會的改革者
當時的阿拉伯社會,有極度發展的阿拉伯部族文化。一個人的社會認同感完全得自於部族的成員身分,而身為部族的一分子,就意味著一定要參與所有的部族活動,尤其是跟麥加宗教經濟系統相關者。然而七世紀時,在貧富差距逐漸擴大之下,阿拉伯部族原本彼此照顧的精神,已在經濟發展中逐漸淪喪,而社會則愈來愈由少數權貴(尤其是古萊須人[Quraysh])所控制,依照著少數菁英部族的利益優先來制定生存法則。由於戰亂、遷徙以及資源分配不均,優勢族群壟斷著阿拉伯社會的運作。所有的窮人、沒有正式保護者的人們(包括孤兒和寡婦等無法取得任何遺產的邊緣人)若要生存下去,唯一的選擇,就是以極高的利息向有錢人借貸,導致債臺高築,陷入萬劫不復的貧窮,最後只好淪為奴隸。
這樣的阿拉伯社會,令當時的穆罕默德相當反感,並造成經商致富的他極大的精神痛苦。因而,穆罕默德時常感到無法原諒自己身為這個利益結構之共犯。阿斯蘭便如此說道:
一方面,〔先知穆罕默德〕以為人慷慨、經營事業公正無私而出名。即使已經成為備受尊敬且相當富裕的商人,他還是經常獨自到麥加谷地周圍的山區與峽谷進行「自我合理化」的閉關修行(也就是上一章裡提到的異教習俗「塔哈努斯」),並且定期在一種跟卡巴信仰關係密切的宗教慈善儀式中捐錢與食物給窮人。另一方面,他似乎也深切意識到自己是麥加宗教經濟系統中的共犯,剝削城內未受到保護的大眾來維持菁英階級的財富與權力。他因為自己的生活方式與信仰不符而飽受煎熬十五年;到了四十歲時,他在精神上已然痛苦不堪。接著,公元六一○年的某個夜晚,在希拉山(Mt. Hira)上進行宗教閉關修行的穆罕默德有了一場將會改變世界的奇遇。
若從這個觀點看來,《古蘭經》的開端,也就是穆罕默德最初接受到的神的話語,其實正蘊含著深刻的政治經濟批判與社會正義的精神。在神最初給穆罕默德的話語中,首先是用美得驚人的韻文歌頌真主的力量與榮耀(《古蘭經》之於阿拉伯文,如同莎士比亞之於英文),接著就是集中在批評麥加部族倫理之淪喪。穆罕默德傳述了採用最強烈字眼來譴責人們對弱者與無依者的虐待與剝削的訊息。他呼籲人們終結讓窮人淪為奴隸的虛假合約與高利貸行為,禁止他的跟隨者任意趕走乞丐與孤兒寡母。他談及弱勢與受欺壓者的權利,並且提出一種新型的、平權的、脫離部族的自由社會。因而,伊斯蘭批評資本主義的利息制度這個當代廣為人知的教義(尤其在二○○八年由美國次級房貸導致的全球金融風暴之後),其實在伊斯蘭形成初期,就已經具備強烈的雛形。
因此,伊斯蘭的建立,是一種對社會不平等的反抗。投入穆罕默德的伊斯蘭運動,意味著身為一個部族成員不僅要改變信仰,還要棄絕部族的活動,本質上就是要脫離部族。這對部族權貴古萊須人而言,是個嚴重的威脅。他們對穆罕默德的主要怨言(至少公開上),早就超越了他對社會與經濟改革的訴求(雖然他們很可能也被那些批評搞到面紅耳赤),也不只限於他激進的一神論(畢竟他們早就習慣不理會信奉一神「異教」的哈尼夫信徒[Hanifs]的那些論調)。阿斯蘭指出,如同貝爾(Richard Bell)所指出的,整本《古蘭經》裡,絲毫沒有半句提到古萊須人基於信念捍衛多神論的話語。反之,就像他們對朝聖者的警告所顯示的,比起傳播一神論訊息,比較讓古萊須人困擾的是穆罕默德不斷抨擊他們祖先的儀式與傳統價值觀,而麥加的社會、宗教與經濟基礎都是建立在這些傳統之上,古萊須人的優勢也緊繫於此。
從這個角度而言,部族貴族古萊須人並不是像一般狹隘的宗教衝突論者常提及的,只是堅持自己的多神論而討厭穆罕默德的一神論,或基於想要捍衛多神論,因此試圖迫害穆罕默德。如阿斯蘭所言:
切莫忘記,古萊須人在宗教這方面的經驗很豐富。他們畢竟靠這個討生活。多神論、單一主神論、一神論、基督教、猶太教、祆教、哈尼夫信仰、各式各樣的異教,古萊須人全都見識過。很難相信他們會因為穆罕默德的一神論宣言而感到震驚。
同樣的一神論調調,當時流行多時的哈尼夫教徒已經講了好多年。所以古萊須人不怕這些「一神教異端」。古萊須人真正怕的,是穆罕默德的社會革命,因為穆罕默德當時所夢想的是一個新社會,而要讓這個新社會可以成立的唯一方法,就是推翻麥加引以為基礎的宗教經濟系統。
以更精準的歷史脈絡分析破除刻板印象
從上述的伊斯蘭發跡是建基在社會改革的訊息中,我們可以發現,伊斯蘭的興起,與建立一個更平權的社會的夢想息息相關。這個重要的觀念,與許多西方媒體以及某些古老西方知識分子所賦予伊斯蘭的形象(拿著刀的武士、血腥狂熱的暴徒)完全不同。阿斯蘭在書的後半部提到:伊斯蘭教於公元六至七世紀在阿拉伯世界興起,雖然穆罕默德帶著關於道德責任與社會平等主義的革命性訊息,卻漸漸地被他的後繼者重新詮釋成各種互相競爭的意識形態,甚至淪為講求嚴格的律法主義與不可動搖的正統。穆斯林社群經過了十八、十九世紀的殖民主義經驗後,每個派別也都有不同的反應。確實,被殖民的經驗迫使整個穆斯林社群重新思考信仰在現代社會中的角色。二十世紀殖民主義結束但西方勢力仍然主導中東政治,儘管遠在東南亞的印尼做為世上最大的穆斯林多數國已經成功轉型為民主國家,中東的穆斯林社會則在困境重重的環境中持續爭辯是否有可能形成一個真正的伊斯蘭民主政體。在這樣的背景下,各方人馬都精進了他們的論點,但這是一個未完的旅程。
但這有那麼令人意外嗎?基督教的改革,當年所帶來的暴力又血腥的戰爭,讓歐洲足足有超過一個世紀時間都陷於破壞與戰亂之中。而且,他們當時並不需要面對外敵時時刻刻的軍事殖民與文化殖民。到了二十世紀,在民主的發展走火入魔成為民粹之後,歐洲在短短幾年間,就把全世界帶入不只一次的「世界大戰」之中。那些頌揚歐洲等於人權與文明,穆斯林社會等於違反人權與落後的觀點,是極為偏頗、罔顧複雜的歐洲血腥殖民史與世界大戰歷史的觀點。事實上,後殖民時期的穆斯林多元社群,一直都在各個國家內部進行各種奮鬥。這些複雜的現象絕對無法以簡化的「文明衝突」來說明。文明衝突的說法,會嚴重地誤導人們本質化某種宗教與文化,進而忽略一直以來,文明與文明之間不斷彼此借用、文明內部充滿更激烈的鬥爭、而跨越文明的權貴階層(包含外來殖民者與本土上位者)總是聯合壓榨雙邊的下層人民(包含帝國本土的勞工階級與殖民地的中下階層)的真實情況。
因此,我們又來到了這個今日屢見不鮮的雙重標準問題:為什麼那麼多的人總是選擇妖魔化伊斯蘭?阿斯蘭又如何在本書中應對這些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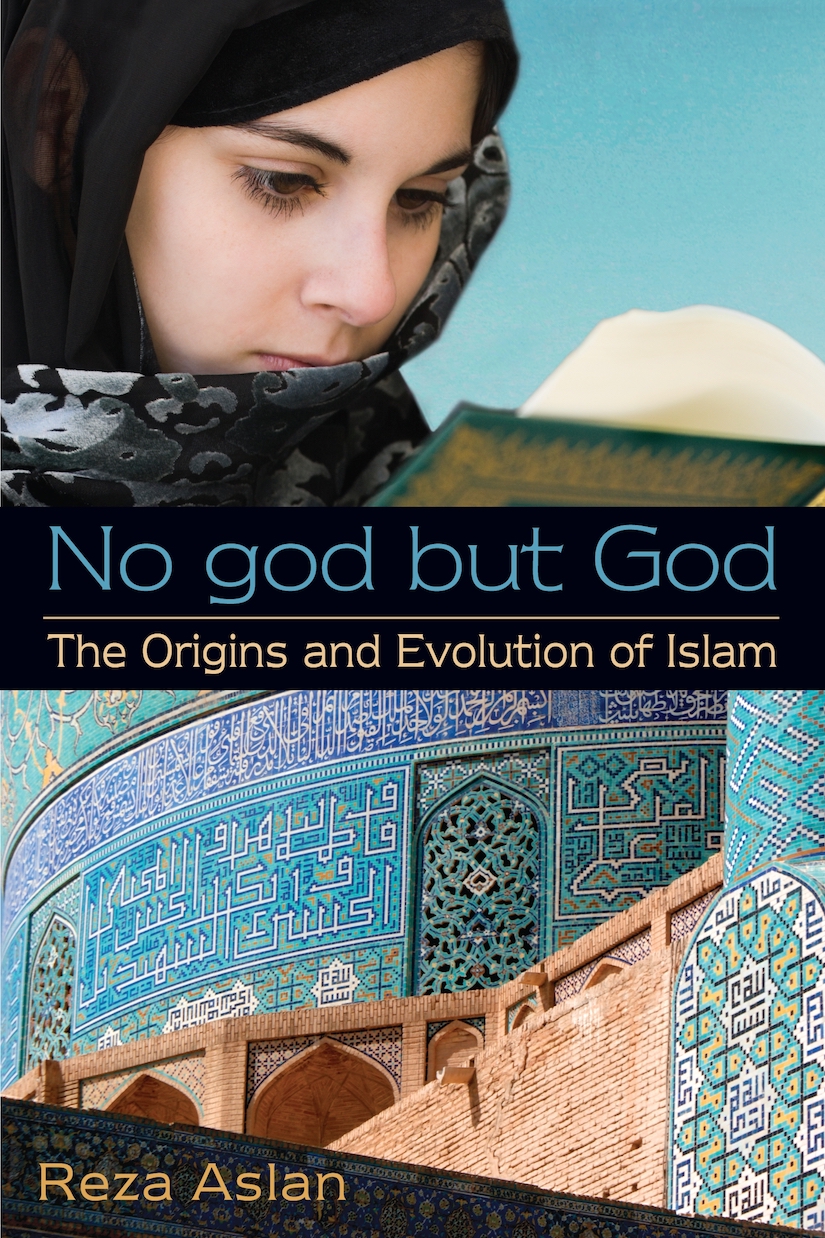
有些人以為,一天要禱告五次,很奇怪。不吃豬,很奇怪。但是,聖靈懷胎,不奇怪嗎?三位一體,不奇怪嗎?或者,乩童可以讓神明附身,不奇怪嗎?
對這類迷思的處理方式,阿斯蘭同樣用歷史考證與比較研究來處理。他舉了以下這些例子說明:聖靈懷胎的故事,其實早就在中東兩河流域盛行已久;在基督誕生前一千多年,瑣羅亞斯德就開始布道說會有一場肉身的復活;「三位一體」的教義是公元四五一年迦克墩大公會議(Council at Chalcedon)的會議結果,在此之前神學家懷疑《新約》中並沒有清楚提及三位一體的概念(這個詞是由最早、最傑出的教父之一,迦太基的特土良〔Tertullian of Carthage〕於公元三世紀時發明的)。如果只看這些「奇怪的」會議所決定的結果,為什麼人們不會去質疑,基督教為何要採用這些奇怪的教義?
顯然,問題不在於什麼宗教信仰比其他宗教更奇怪,而是在於為什麼我們只會質疑、詰問某些宗教,卻默認其他宗教的合法性。
有些人以為,伊斯蘭是一個有問題的宗教,而穆斯林是「穿著長袍、亮出彎刀、準備隨時宰了出現在他面前的異教徒」的瘋狂人類。這些意象從九百多部好萊塢電影以及迪士尼卡通都可見到。對此刻板印象的回應,阿斯蘭的話語非常精闢有力,清楚描述人們是如何使用完全雙重標準的方式來理解十字軍東征以及伊斯蘭帝國的擴張,在此容我大幅引用:
伊斯蘭教是誕生在一個強盛帝國與全球擴張的時代,當時拜占庭帝國與薩珊王朝─兩者皆是政教合一的王國─都為了擴大疆域而陷於一種時時都在進行宗教戰爭的狀態。擴張到阿拉伯半島之外的穆斯林大軍只是加入了原本就已存在的混戰;雖然他們很快就占得上風,但這場混戰既不是他們發起的,也不是由他們來定義的。儘管西方人普遍認為穆斯林征服者強迫被征服的民族改信伊斯蘭教,但穆斯林征服者並未這麼做;實際上,他們甚至不鼓勵這麼做。真相是:在第八和第九世紀,阿拉伯穆斯林擁有極大的經濟與社會優勢,因此伊斯蘭很快就變成一個菁英集團,非阿拉伯人只能透過一套複雜的程序加入,首先就是要成為阿拉伯人的依附者。
這也是個宗教與國家不可分割的年代。除了寥寥幾位與眾不同的男女之外,這個時代沒有任何猶太教徒、基督徒、祆教徒或穆斯林會認為自己的宗教源自個人私密的自白經驗。事實恰恰相反。你的宗教就是你的種族、你的文化、你的社會身分,它定義了你的政治、你的經濟情況、你的道德倫理。最重要的是,你的宗教就是你的「國籍」。因此,神聖羅馬帝國有其官方認可並依法實施的基督教版本,如同薩珊帝國也有其官方認可並依法實施的祆教版本。在印度次大陸,毗濕奴諸王國(毗濕奴及其化身的信奉者)與濕婆諸王國(濕婆神的信奉者)競相爭奪領土的控制權,而在中國,佛教統治者也和道教統治者爭奪政治優勢。在所有這些地區,尤其是在國家明顯由宗教支持的近東地區,領土擴張與宗教傳播完全是同一件事。因此,「每一個」宗教都是「劍之宗教」。
當穆斯林征服者開始闡述伊斯蘭教的戰爭意義與戰爭作用時,他們手邊就有一些非常成熟的宗教戰爭理想可以套用;這些發展成熟的理想受到帝王支持,薩珊和拜占庭帝國都在實行。事實上,「聖戰」(holy war)一詞並不是源自伊斯蘭教,而是源自基督教十字軍,他們率先用這個詞賦予戰爭神學上的正當性,但打仗其實是為了爭奪土地和貿易路線。穆斯林征服者並未使用「聖戰」這個詞,而把阿拉伯文的「吉哈德」(jihad)定義成「聖戰」也完全不恰當。阿拉伯文中有許多字詞可以毫無爭議地被翻譯成「戰爭」,但「吉哈德」不在其列。
其實,把jihad翻成「聖戰」是沿用西方媒體理解的方式,而這在穆斯林法學者與伊斯蘭研究中仍然是富有爭議性的概念。Jihad字面上的意思是「努力、奮鬥」,且往往有兩種以上的意涵,至少分為「為抵抗外敵侵略而戰」或「奉主命成為安拉喜悅的行為,或說是心靈克服欲望野心的征戰」。此外,《古蘭經》與聖訓章節其實有許多提倡和平、禁止濫殺無辜市民(任何有女人小孩的地方都不准許,即使在戰場上也不允許、對和平者也不可施加暴力、也不可對勞工施加暴力、即使在戰場上也不允許)的訊息。在這樣的理解中,「自殺炸彈客」或「濫殺無辜」幾乎很難找到伊斯蘭的基礎。
阿斯蘭就指出,以古典吉哈德信條來說,把世界分成「伊斯蘭之土」(dar al-Islam)與「戰爭之土」(dar al-aharb)的對抗,是從十字軍東征後延伸而來的觀念,其實是一種特定戰爭時期的歷史產物,卻被後世當成了不可動搖的教義。但阿斯蘭在書中也舉出,當十字軍東征結束,古典吉哈德信條就已經受到新一代穆斯林學者的激烈挑戰。伊本─泰米亞(Ibn Taymiyya,一二六三─一三二八)就堅稱,殺死拒絕改信伊斯蘭教的不信道者─古典吉哈德信條的基礎─不但跟穆罕默德的典範背道而馳,也違反了《古蘭經》中最重要的原則之一:「對於宗教,絕無強迫」(2:2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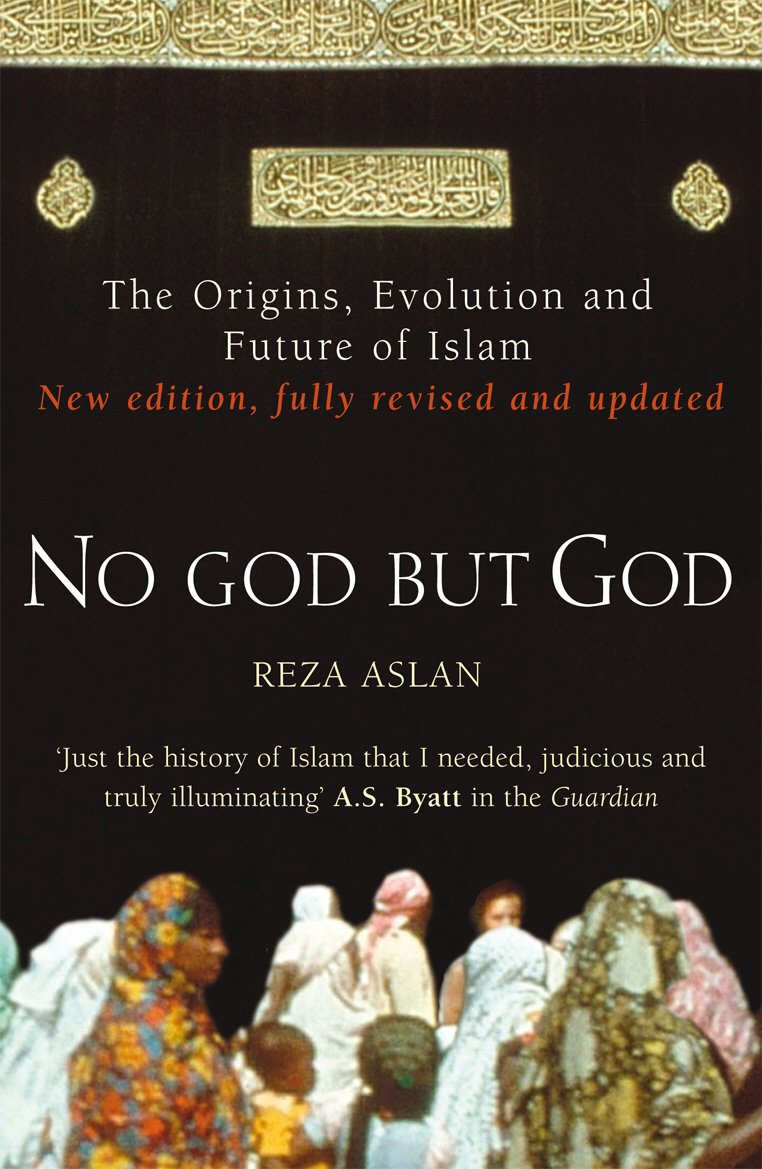
另外一個關於伊斯蘭根深蒂固的錯誤偏見,是以為伊斯蘭要求政教合一。然而,如同Robert Hefner教授在《公民的伊斯蘭》(Civil Islam)一書的導論所提及的,歷史中充滿著豐富的、穆斯林社群實行政教分離的經驗。事實上,《古蘭經》也從未提出一種關於國家的政治理論。阿斯蘭指出,如同許多穆斯林法學者已經指出的,先知權威應該僅限於真主使者的宗教職責,而哈里發的職權則純屬世俗,所有的穆斯林都可以質疑、反對、甚至反抗。阿布杜─拉濟克(Ali Abd ar-Raziq)甚至會說,伊斯蘭教的普世性只能以它的宗教與道德原則為基礎,跟個別國家的政治秩序完全無關。因此,阿斯蘭提醒我們,當代我們看到的那些似乎在進行政教合一的國家,他們是穆斯林社群中很晚近才出現的異類,與幾百年來多宗教多種族多文化的鄂圖曼帝國經驗完全不同,是各種新型的後殖民現代實驗:
〔別忘了世界各地許多穆斯林社群早就與民主和平共處多時,但如果是真的〕想把沙里亞納入法律系統,現代伊斯蘭國家只有三種選擇。可以完全採用傳統主義者對沙里亞的解釋,既不嘗試讓它現代化,也不配合當代的法律與社會常態來調整它,例如沙烏地阿拉伯和塔利班政權底下的阿富汗就是如此。〔但這是很晚近的發展,甚至可以說是歐洲殖民、鄂圖曼解體之後的結果。〕或是可以接受傳統主義派對沙里亞的觀點,說它是民法的合法法源,但除了關於家庭、離婚或繼承等最明顯的案例之外,完全不予採用,埃及和巴基斯坦就是這樣。或者,也可以嘗試透過一套全面性的改革方法,將沙里亞的傳統價值與立憲主義及法治等現代原則融為一體,同時考慮它的歷史背景和它在人類手中的演進。除了伊拉克發展迅速的民主實驗之外,目前只有一個國家〔伊朗〕認真考慮最後這個選項。
由此來看,現代的某些極權國家,在後殖民或是西方扶植過魁儡政權的政治境況下、試圖將伊斯蘭律法(沙里亞)進行法典化甚至套用在刑法上─畢竟,一直以來,伊斯蘭律法最重視的範圍是民法、地位法、財產繼承以及商業法規,而非刑法─都可說是一種現代的發明。如阿斯蘭所言:
就算只是對沙里亞的發展進行最初步的分析,也足以證明法律和天啟都是「和伊斯蘭社群一起」成長的……穆罕默德的公社演變時,啟示就隨著公社的需求改變。事實上,在穆罕默德管掌權的二十二年裡,《古蘭經》幾乎時時都在變。
阿斯蘭所謂的「時時都在變」,指的是神的啟示是來自回應於人民的呼喊,而神的回應也總是照顧到人民在不同脈絡下的需求而精於變通。遺憾的是,許多人忘記了伊斯蘭律法幾百年來有著多重法源且內建多元彈性的歷史,反而選擇採取了基督新教某種literalist(望文生義而排除脈絡)的閱讀《聖經》的方法來閱讀《古蘭經》。這樣的發展,對於如阿斯蘭這樣的學者以及其他許多鑽研伊斯蘭法學的學者而言,不但無法體會伊斯蘭的平權之夢,甚至可以說是與伊斯蘭提倡的最基本的社會改革精神背道而馳。
最後一個根深蒂固、歷久不衰的迷思,是伊斯蘭歧視女性的觀念。關於《古蘭經》如何重視女性的權利,已經有非常多穆斯林女性主義的經典鑽研,在此不贅述。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今年《新世紀宗教研究》最新一期期刊(第十六卷第三期)中,我針對Amina Wadud的穆斯林女性主義經典Qur’an and Woman所寫的書評與每章摘要。幾乎所有針對伊斯蘭與性別的爭議(包含一夫多妻在何種嚴格條件下才可行、女性是否可以擔任國家領袖、男尊於女是否真受《古蘭經》支持、女性證人是否不如男性證人、分財產規則是否只限男多於女等等),都可以在這本書中獲得解答。其實,歷史上對於《古蘭經》採取偏頗的男尊女卑的解釋,起初是來自於男性法學者試圖利用他們的宗教與政治權威,好奪回他們因為先知的平等主義改革而失去的社會優勢;以及後世盲目地「傳承」這些不平等的做法,好維持他們既得的利益。上述這些反對性平改革的發展,對於許多穆斯林以及鑽研伊斯蘭律法的學者而言,都違反了真正的伊斯蘭精神。以阿斯蘭的話語來說,先知穆罕默德所提倡的,是以下的社會圖像:
女性主義者眼中的麥地那是一個這樣的社會:穆罕默德任命像烏姆─瓦拉卡(Umm Waraqa)這樣的女性為溫瑪的精神導師;先知自己有時也會被妻子公然訓斥;女人和男人並肩祈禱作戰;阿伊夏與烏姆─薩拉瑪這樣的女子不只擔任宗教領袖,也是政治領袖─而且至少當過一次軍事領袖;而當召喚眾人祈禱的聲音從穆罕默德家的屋頂上大聲傳出時,男男女女齊聚一堂、並肩跪下,毫無隔閡,以一個團結的公社之姿接受神的賜福。
給平權鬥士的一份禮物
這本書當然不是沒有缺點的。首先,從許多西方進步媒體對本書的書評中可以看出,西方評論家誤以為阿斯蘭所提到的改革是一件很新穎的事情,但事實卻完全不是這樣。改革這件事情在伊斯蘭的歷史中已經出現過太多次,每次有了保守反改革運動之後,也會有改革運動,而改革運動自己本身也可能變成另外一種新權威,而在未來必須接受新的挑戰。事實上,主張這些變革所需要的基礎,不論是在「伊斯蘭法學研究之父」Joseph Schacht、Schacht 的高徒與最有力的批判者Noel Coulson,或是穆斯林女性主義學者Fatima Mernissi與Amina Wadud,以及宗教學者Asma Barlas的學術著作中,都有更詳盡更嚴謹的論證。因此,如果說對西方媒體而言,阿斯蘭可能會被當成伊斯蘭內部的「異端」的話,在伊斯蘭研究的國際學術界中,阿斯蘭的視角並不特殊。差別只在於,寫給大眾看的書寫,與需要更多嚴謹的證據引用與學術論證來支持特定歷史詮釋的書寫,終究是天壤之別。但不論是哪一種書寫,都必須有所取捨。對後者而言,這本書並未帶來一種革命性的想法,而只是暴露出學術界的象牙塔與西方主導的媒體下的公共知識分子之間仍然存在的巨大鴻溝。
當阿斯蘭試圖去彌補這個鴻溝時,他或許可以更清楚地反覆告訴讀者,其實他的這些脈絡性重讀經典與重構歷史的視角,老早就已經被許多當代學者同意,甚至是伊斯蘭研究的前提。他或許可以更積極反覆地告訴讀者,改革不是最近才發生的事情,也不是他個人發難提出的,而是一開始就是伊斯蘭的核心價值,但在先知後人手中逐漸成為了反改革運動。之後,在鄂圖曼帝國開始逐漸受到西方威脅、乃至十九世紀乃至二十世紀時,其實從中東到東南亞,每個世紀都有伊斯蘭改革。讀者之所以會誤以為阿斯蘭提出的是「革命性的」,嚴格來說並非阿斯蘭的錯,而是由於西方知識份子長期對於伊斯蘭世界的想像過於固定僵化,乃至於他們在紐約時報或衛報等看似西方最進步的媒體上回顧本書時,仍然脫離不了「伊斯蘭需要的是一場啟蒙運動」或是「改革之聲是例外、堅持正統才是常態」等將伊斯蘭孤立於西方歷史並將其視為一個現代性的「例外」的錯誤預設。改革不被重視往往是政治問題,而非單純的宗教問題。而究竟何謂正統?將晚近的沙烏地阿拉伯的現狀,錯誤地投射為伊斯蘭的正統與本質,進而忽視幾百年來伊斯蘭在世界各地的多元容忍面貌,是西方讀者最常犯的錯誤。阿斯蘭強調文化融合與對政治經濟狀況有所回應的伊斯蘭,便在這些高端西方知識分子的理解中被默默地埋葬了。既然這是一本寫給西方讀者的書,卻不能更進一步地瓦解讀者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顯然是背後有更大的歷史意義結構使然,並非完全是阿斯蘭不夠用力才導致西方讀者誤讀。
這本書的另外一個缺點,同時也是其他學術性解構經典或歷史重構之研究的缺點,就是與當代生活脈絡的脫鉤。比如,已經有太多歷史證據與伊斯蘭法學研究指出,穆斯林女性必須配戴頭巾是一種「共識」(伊斯蘭律法的法源之一),也就是穆斯林學者決議的結果,並非來自《古蘭經》或聖訓。但這樣專注於經典的解構,卻無法說明一九七○年代以降,大規模出現於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社群「重新戴上頭巾」的運動。同樣的,這種學術解構,依然無法回答,為何在穆斯林女性主義運動後,仍有大量的女性主動服膺於父權的《古蘭經》解讀而非性別平權的經文詮釋?像阿斯蘭這樣的解釋,對於那些真正生活在不得不為自己的家園「奮鬥」而在西方話語權下變成「聖戰士」的人們,有什麼幫助可言?這也就是說,專注於經典的原汁原味重現並更公平地重構一段歷史,本身也只是一種視角,而無法據此就進入到人們生活的真實脈絡。恐怕只有人類學與社會學的民族誌研究,才有辦法清楚回答,究竟人們與其宗教認同以及信仰故事的關係是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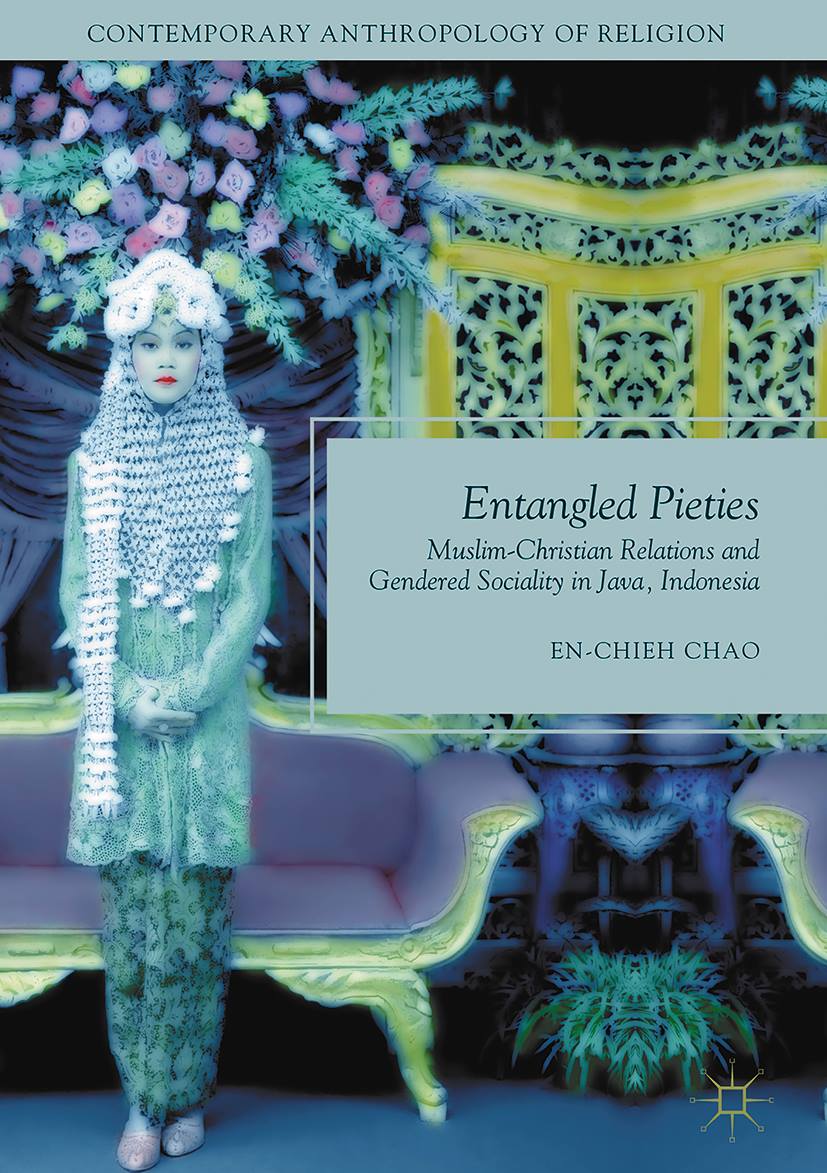
雖然有以上這些缺點,但這不會因此掩蓋了這本書支持大膽前進的改革精神。這本書值得推薦給所有人,不論你對伊斯蘭的理解是零、負五十,或一知半解。即使是精通伊斯蘭歷史的學者,也能夠從這本書中,看看阿斯蘭如何與有著不同關懷的現代公民們溝通,並將知識說成一個流暢的故事。更重要的是,這本書非常適合做為給所有平權鬥士的一份禮物。地球上的所有政權都來來去去,偉大的不過數百年。然而無論是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這些都是上千年的流動的人類遺產。一千年後也還會存在。在瞬息萬變的今日,瞭解一份橫跨千年的毅力與傳承之心,特別適合在世間炎涼中孤單行走的平權鬥士們。
僅以這篇導讀,獻給所有在平權之夢路上奮鬥而互相依偎的人們。
西子灣
二○一八年七月十二日
(本文亦刊載於《伊斯蘭大歷史》作為導讀)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趙恩潔 伊斯蘭的平權之夢:論雷薩.阿斯蘭的《伊斯蘭大歷史》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676 )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