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語言來
語言人類學導論》導讀
想想下列三個場景:(1)父母親從學校把他們的小孩接回家;(2)一對年輕情侶的第一次約會;(3)一位男性第一回見到他的新同事。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區,尤其是美國電影和電視節目中,這些場景皆有一共同點:參與者之間會需要交談。他們之間的談話氣氛可能會是氣憤的、緊張的、尷尬的或自吹自擂的;但無論如何,他們唯一不會做的事就是彼此之間保持沉默!父母可能會詢問他們的小孩有關學校的課業,或者他的朋友;這對年輕情侶會努力做出緊張的小談話;這位男生會在介紹自己的時候大力地握住新同事的手,甚至可能會開個玩笑作為兩人初次見面的破冰。但是在1960年代後期美國的阿帕契西部地區(Western Apache),阿帕契人的反應是很不同的。 如克斯.巴索(Keith Basso 1970)的經典民族誌所描述,在上述情況中,阿帕契人很可能會保持沉默。對於大多數美國人來說,在這些情境保持沉默會讓人感到尷尬和不舒服,但對於西部的阿帕契人來說,打破沉默會令人感到更為尷尬。
巴索的研究是當代語言人類學方法論中有著卓越貢獻的一個重要範例:溝通民族誌(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雖然標準的語言分析的工具可適用於分析西部阿帕契語,如透過音韻學、構詞學、語法學等,但是若以這些方法對阿帕契人沉默的使用進行調查,仍然不夠清楚、完整。語言學試圖瞭解能產生無數話語的基本結構,而溝通民族誌則試圖瞭解影響特定談話行動的潛在文化邏輯。兩門學科的差異在於,就如同英語使用者知道在單詞cat中添加上s,使這個單詞變成複數,以及知道當他的朋友說「我愛貓!」(I love Cats!)時,實際上指的是著名百老匯音樂劇,這兩者間的區別。雖然所有說英語的人都知道如何區分單數和複數,但是只有那些具有百老匯音樂劇特定文化知識的人才會知道,「我愛貓!」這句話可能指的不是對毛茸茸寵物的普遍性喜愛。因此,西部阿帕契人之間的沉默可以用同樣的方式來看待。因為沈默是沒有話語的,所以沒有語法規則來管理沉默的語言結構,但是在保持沉默的情況之下,說話者已做出在該社會中具有文化意義的一種選擇,即決定在這種情況下是否需要說話。唯有對西部阿帕契人的文化規範有全面性的瞭解,才能正確解釋這種沉默的意涵。反過來也是如此,瞭解沉默也可以教導我們關於阿帕契文化的一些東西。舉例來講,想想「大人說話,小孩別插嘴」(children should be seen and not heard)這個說法吧。這句話告訴我們,兒童在特定社會中應該扮演什麼角色,而那個社會也把這種說法當成基本常識來接受。
為了理解西部阿帕契人如何使用沉默,我們需要知道些什麼?巴索告訴我們的方法是,在保持沉默被認為是合適的一系列情境中,尋找出潛在的相似性。除了上面列出的三種情境(從學校接小孩回家、約會和遇到陌生人之時),巴索還發現了西部阿帕契人在另外三種情境中,他們也會保持沉默:「被惹惱時」、「與悲傷的人在一起時」,以及當「他們一起唱歌時」。(巴索對這些情境所下的英文標題,都是他根據他的研究對象們用西部阿帕契語所講述的內容之直接翻譯。)第一種情境指的是一個人正站在一群生氣的人旁邊,這群人正在大喊大叫或正在詛咒每個人,無論那些人是否應對他們的憤怒負起最初的責任(Basso 1970: 221-222)。第二種情境指的是一段過渡期,其介於極度哀傷時期與準備開始重新融入社區的時期(p. 222-224)。第三種情境指的是由熟悉傳統醫術的人進行的治療儀式(p. 224-225)。巴索在檢視所有這六種情境之後做出的結論是,這些都是社會關係無法預測的情境,可能是因為另一個人是真正的陌生人,也可能是因為那個人經歷了某種轉變。也就是說,這些都是現有的「社會行動的指南」無法有效運作的,而且「必須暫時捨棄或突然修正」的情境(p. 1970: 227)。
巴索的民族誌不僅揭示在西部阿帕契社會中對於沉默的文化意義,也揭示了西部阿帕契社會與「昂格魯」(Anglos)(他們對於美國白人的稱呼)關係的更深層意義。這可以從他們保持沉默的六種情境之中的兩種看出來。 第一種情境是遇見陌生人。當一位昂格魯開始與一位陌生人交談時,西部阿帕契人認為他只是「想教我們一些東西」(Basso 1970: 218)。這反映了在阿帕契地區定居的美國白人與當地阿帕契人之間的殖民歷史,其中昂格魯人通常只給阿帕契人命令,或者試圖改變阿帕契文化。 這也解釋了為何阿帕契人會對從寄宿學校返家的孩子們保持沉默。建立寄宿學校的機構是一個相對較為現代的發展,寄宿學校最初在美國印地安人地區建立的理由在於「印第安不滅,人性不彰」([Killing] the Indian, save the man)(Pratt 1973: 260)。也就是說,它打算完全根除美國印地安人的文化,將阿帕契學生加以「文明化」。這是以學校作為殖民化的實踐結果,父母有理由擔心他們的孩子從學校回到家後,可能不再對他們的父母或是他們的文化保持著像過去一般的尊重。或者,正如巴索的一位報導人所說,「在學校,他們之中的一些人想要學會成為白人,所以他們回到家試圖這樣做。但我們仍然是阿帕契人!因此,我們不再瞭解那些人,就像我們從來不認識他們一樣」(Basso 1970: 220)。出於這個理由,阿帕契人在跟他們的小孩交談之前,需要花一些時間觀察他們,以便充分判斷他們的小孩對自己文化的態度是否產生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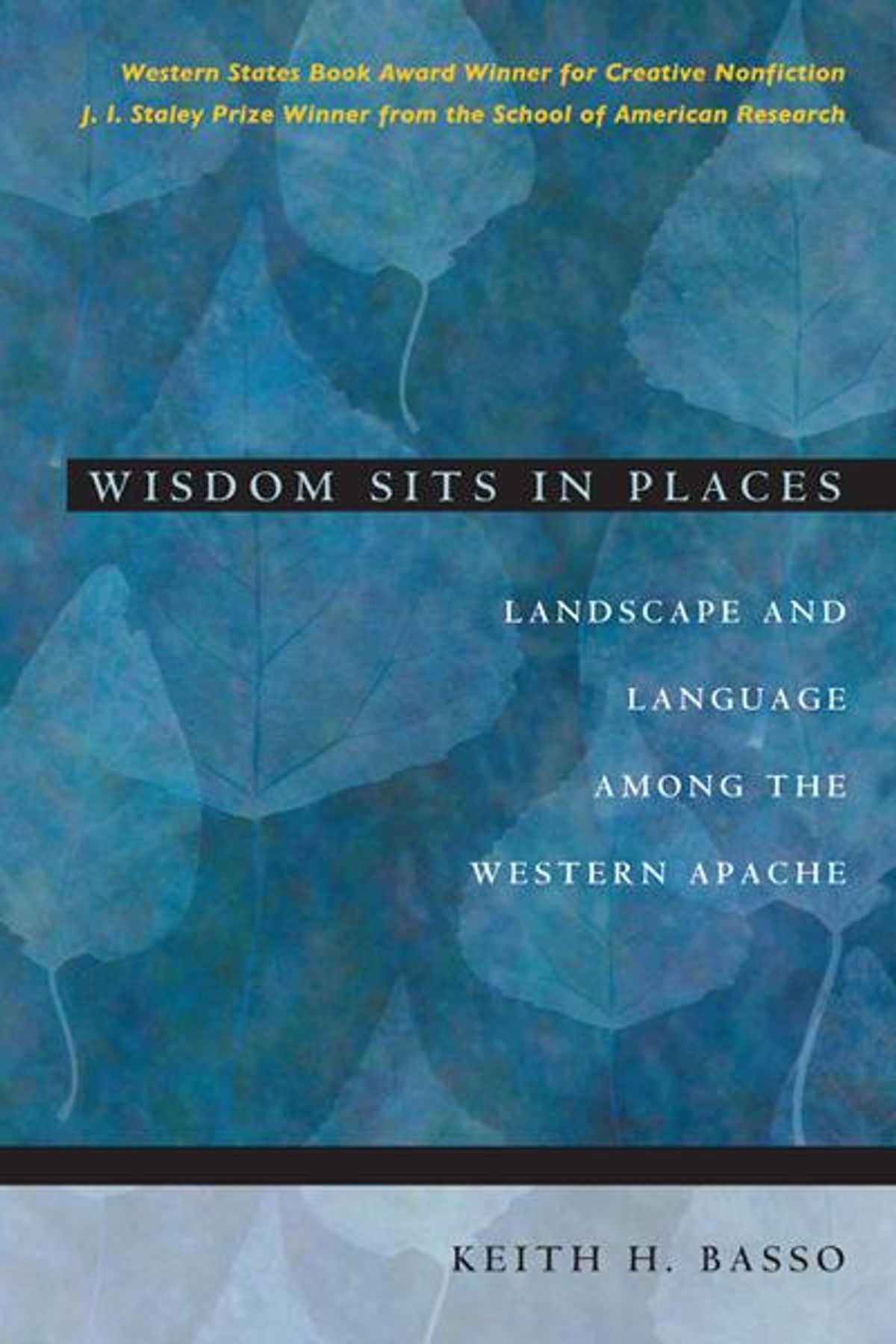
巴索有效使用的「溝通民族誌」,是由戴爾.海姆斯(Dell Hymes)和其他人在1960年代早期發展出的理論架構,當時,語言學界的喬姆斯基學派革命(Chomskyan revolution)也恰好開始發展。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強調不管語言或文化上的差異,所有健康的人皆共享了普同的「語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而海姆斯則專注於文化上特定的「溝通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語言能力指在語法上正確地表達出話語的能力,這種技能是大多數健康的人類兒童在小時候獲得的。另一方面,溝通能力涉及許多具有文化意義的特殊技能,這些技能必須針對每一特定脈絡和談話文類而重新學習,並且同一語言的所有語言使用者並不一定獲得這些技能。從學校教科書中學會西部阿帕契語的人可能具備語言能力,但他們不一定具備溝通能力,瞭解某些人的沉默。巴索的研究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告訴我們民族誌如何成為一重要窗口,用於理解這些具有文化意義的特殊能力。
正是因為溝通民族誌開闢了喬姆斯基學派的語言學所忽略的諸多領域,它進一步將這兩個學門分開,而其他力量也已經將這兩個領域推向不同的方向。早期的語言人類學家和語言學家經常有著密切的合作。法蘭茲.鲍亞士(Franz Boas)是美國人類學的創始人之一,他曾擔任過美國人類學學會(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AAA)和美國語言學學會(Language Society of America, LSA)的主席(Black 2014)。他的兩位學生阿爾法雷德.克羅伯(Alfred Kroeber)和愛德華.薩皮爾(Edward Sapir)的情況也是如此,但是海姆斯是最後一個擔任這兩個職位的人,因為這兩個領域在1960年代開始出現分歧。受到常被稱為「喬姆斯基學派革命」的影響,美國的語言學發展變得更加抽象和數學化的導向,而語言人類學家則強調語言行為被嵌入社會的面向。有跡象顯示這樣的發展可能會再次發生變化。喬姆斯基學派的語言學從來就不是語言學的唯一形式,儘管該學派的支持者在某一學術時期成功地說服大家喬姆斯基學派是唯一的重要語言學派(Harris 1995)。事實上,語言學的學科內一直存在許多不同的學術傳統,其中的一些傳統能更貼近於民族誌的方法。事實上,一些學者相信「一股新空氣已進入語言學的領域」,並「透過調查世界上不同語言的細節,可獲得令人興奮的新發現」(Ibbotson and Tomasello 2016)。丹尼爾.艾弗列特(Daniel Everett)就是這樣一位學者,他在巴西的皮拉哈族(Pirahã)地區工作,他的研究對於一些喬姆斯基學派的核心思想的語言學取徑已經提出懷疑。艾弗列特強調的是「試圖在儘可能接近原來的文化脈絡的情況下,瞭解語言」(Everett 2009: 243)。他的說法暗示了兩個學科之間可能存在的合作關係。
當一些語言學家開始接受文化在語言中的地位之時,文化人類學正轉向接受語言在文化中的地位。許多人認為《寫文化》(Writing Culture)一書(Clifford and Marcus 1986)是人類學在「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上的里程碑式文本,這本書更關注於人類學知識受到語言形塑的方式。例如:訪談本身需要被視為「溝通事件」進行分析,它不僅僅是「一個透明的窗口,研究人員可以通過該窗口獲取事實或訊息」(Ahearn 2017: xii)。文化人類學家越來越能自我反思地看待他們的資料是如何被收集、被處理和被轉化為民族誌文本的過程,語言人類學家所開發出的研究方法和理論工具,已從語言人類學專業次領域的出處轉為主流文化人類學知識的重要部分之一。艾倫.拉姆西(Alan Rumsey)記錄了語言人類學與其他學門的合作關係,他表示即使語言人類學學會(Society for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SLA)能穩定地吸引新成員的加入,從1985年的332名成員增加到2010年的兩倍之多,既是語言人類學學會成員也是兩個主要的文化人類學學會(美國民族學會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和文化人類學學會(Society for Cultural Anthropology)成員的人數也在增加中(Rumsey 2013: 269-270)。他總結說「有一大批美國人類學學會的成員自己和其他人認定他們主要是與社會文化人類學相關,但他們也對語言人類學有著濃厚的興趣」(Rumsey 2013: 270)。
這種在人類學不同分支之間的互動和合作是開始在語言人類學發生,由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開始出版的下一代學者中所見到的變化。正如斯蒂芬.默里(Stephen Murray)(1998)的著作《美國社會語言學:理論家和理論小組》(American Sociolinguistics: Theorists and Theory Groups)所記載的,在許多下一代學者之中,他們本身就是海姆斯或他以前在柏克萊大學的同事約翰.甘柏茲(John Gumperz)的學生。(海姆斯待在柏克萊大學幾年之後,離開前往賓州大學。)在賓州大學期間,海姆斯曾在1964年提倡「在人類學脈絡中研究語言」(Hymes 1964: xxii; 見Duranti 2003: 327),對於下一代學者而言,語言「不再是……調查的主要對象」,而是「獲取複雜社會過程的一種工具」(Morgan 2002; 見Duranti 2003: 332)。溝通民族誌已經將語言研究的關注焦點,從較為狹隘的語言結構的形式特徵,轉向將溝通看成社會行動的廣泛觀點,當代語言人類學家正是在這一基礎上發展他們的研究,關注於談話行動如何超越語言本身,「指向」(index)了引發談話行動的社會和文化脈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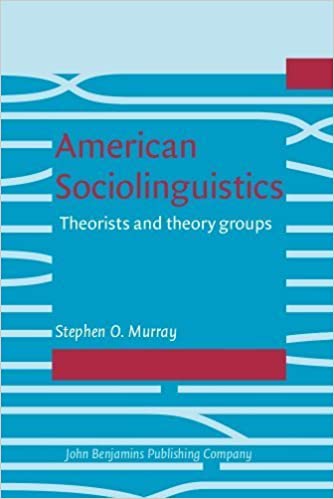
經由指出「超越談話行動本身的一些東西」(Jackson 2013: xxiv),因而語言通常可被運用於再生產或挑戰普遍性的身份認同觀點。這個概念叫做「指向性」(indexicality),一個來自符號學(semiotics)或符號研究的專有名詞。本書作者阿赫恩(Laura M. Ahearn)(2017)強調指向性是全書的四個關鍵詞之一,對於語言鑲嵌於社會的性質,以及社會生活受語言中介的特性,這些概念提供了洞見。其他三個專有名詞是「多功能性」(multifunctionality)、「實踐」(practice)和「語言意識形態」(language ideology)。這些概念有助於說明人類學家對於語言研究提供的獨特貢獻。 語言人類學作為人類學四大分支之一,早已在以中文為主的大學課程中教授;然而,這些課程往往側重於錄音和記錄原住民和少數民族的語言,而不是語言作為社會行動的一種形式。且並不罕見地,這種課程往往由語言學家而不是人類學家來教授。在臺灣的學術界,這些概念很少被廣泛地瞭解或討論,更不用說在更廣泛的中文群眾之間。 因此,透過2018年夏天,在臺灣社群媒體上發生的一個事件的說明,我希望簡要地強調這些概念對於臺灣讀者的實用意義在哪裡。
在2018年夏天,來自花蓮阿美族(Pangcah或Amis)的民進黨立法委員Kolas Yotaka被任命為行政院發言人,阿美族是臺灣十六個官方認定的臺灣原住民族(南島民族)之一。在她被正式任命不久之後,她公開表示她傾向於用拉丁字母來書寫她的名字「Kolas Yotaka」,而不是用中文字「谷辣斯.尤達卡」。在臺灣,使用中文音譯撰寫外國名字是一種常態,即使原住民語言不是臺灣的「外國」,但是原住民語言通常也會受到同樣的對待。在台灣的報紙,美國電影明星Harrison Ford的英文名字通常會被寫成哈里遜.福特,其發音為「Halisun Fute」。由於中文和英文在音韻上的差異,福特只能大略等同於「Fute」。出於類似的原因,Kolas認為中文音譯她的名字谷辣斯.尤達卡無法精準地捕捉到阿美族語(Pangcah)的發音(雅虎奇摩新聞2018)。最值得注意的是,中文的詞構將「Ko-las」的兩個音節變為三個音節「谷辣斯」。為了理解為什麼Kolas的請求會在臺灣的社群媒體上引發了激烈討論,您需要「掌握」的是,能形塑臺灣的語言意義之「社會、歷史和政治力量」,這點非常重要(Jackson 2013: xxiv)。
書寫系統不僅是一種表達語言聲音的方式,它是多功能性的一個良好例證,它是阿赫恩列出的四個關鍵詞中的第一個。書寫系統還可點出(或「指向」)在我們想法中與這些書寫系統關係最為密切的一群人的身份認同(指向性是第四個專有名詞)。在熱愛於學習英語的國家中,英語詞彙經常出現在T恤衫、菜單、商店標誌和廣告牌廣告上,在人們的心目中,拉丁字母與英語的關係最為密切,這點並不奇怪。這就是為什麼在社群媒體上的一些評論,會說到「原住民是說英語的嗎?」(Hioe 2018)。Kolas抱怨她自己有時在醫院需要用英語說話,因為醫院人員認為她應該是住在臺灣的許多外籍家庭幫傭的一員(雅虎奇摩新聞2018)。但將拉丁字母看成不是臺灣的一部分是錯的。事實上,自2017年6月通過「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之後(Kolas她自己就是該法案的主要支持者),在台灣的「原住民書寫文字」皆具有官方地位(2017年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在臺灣,原住民書寫文字也不是唯一使用拉丁字母的文字。正如時代力量的政治人物林于凱在他的臉書上所言(Lin 2018),臺灣的第一份報紙是使用拉丁文來撰寫河洛話(閩南語)。今日只有中文文字被認為是適合用於臺灣報紙的書寫系統,這是導因於數十年以來,臺灣的官方語言政策將漢語視為「國語」。這是阿赫恩所列出的第三個專有名詞「語言意識形態」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她將其定義為「我們所有人對語言的態度、觀點、信仰或理論」(Ahearn 2017: 23)。然而,並沒有語言上的理由可以說明臺灣為何不能像韓國和越南一樣,將中文文字全部消滅掉(Chiung 2007)。若說臺灣人已經將中文文字視為國家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臺灣戰後的一些國家政策,其用意在於對公民灌輸強烈的「中國人」身份認同(Chun 1996)。
但是Kolas名字拼寫所出現的爭論,並沒有因此就停止。第二個議題的出現是源自於對她名字的第二部分Yotaka的討論。Yotaka並不是她的姓,其實是遵循阿美族的慣習,用她父親的名字。由於臺灣以前是日本的殖民地(1895-1945),許多臺灣原住民第一次學會如何閱讀和寫作是在臺灣的日本學校中,甚至許多人認為自己是日本人(Friedman 2010)。 這可解釋為什麼她有一個日本名字,這樣的說法不同於在社群媒體上嘲弄她如何拼寫她名字的議題。一些網民試圖證明Kolas應該自己感到尷尬,因為她拼錯了她的名字Yotaka,使用了「o」而不是「u」。將Yotaka放入網路上的谷歌翻譯功能中,翻譯成的日本片假名為「ヨタカ」,而ヨタカ的中文翻譯的意思是「娼妓」。要是想得到正確的漢字「豊」,需要輸入「ユタカ」,它的拉丁字母通常拼寫為「Yutaka」,其中的一個字母是「u」(Hioe 2018)。雖然從一名日語使用者的觀點來看,這一論點可能是有意義的,但根據原住民社會運動者Namoh Nofu Pacidal的說法,在地阿美族語使用者對這種拼寫並不會有任何疑義(Pacidal 2018)。這是因為(除了阿美族語的北部南勢方言),大多數的Pangcah語言使用者並不區分「o」和「u」的聲音,因此他們傾向於交替使用這兩個拉丁字母。 如果她的名字是用「原住民書寫文字」書寫,而不是「拉丁文」或日文,那麼台灣原住民應該是判斷「什麼才是正確的名字拼寫?」的裁判。最後,許多試圖羞辱Kolas的人,假設了她名字書寫有「錯誤」,似乎是有其政治上的動機,但即使是這樣,這種攻擊只有在與既定的語言意識形態產生連結才有可能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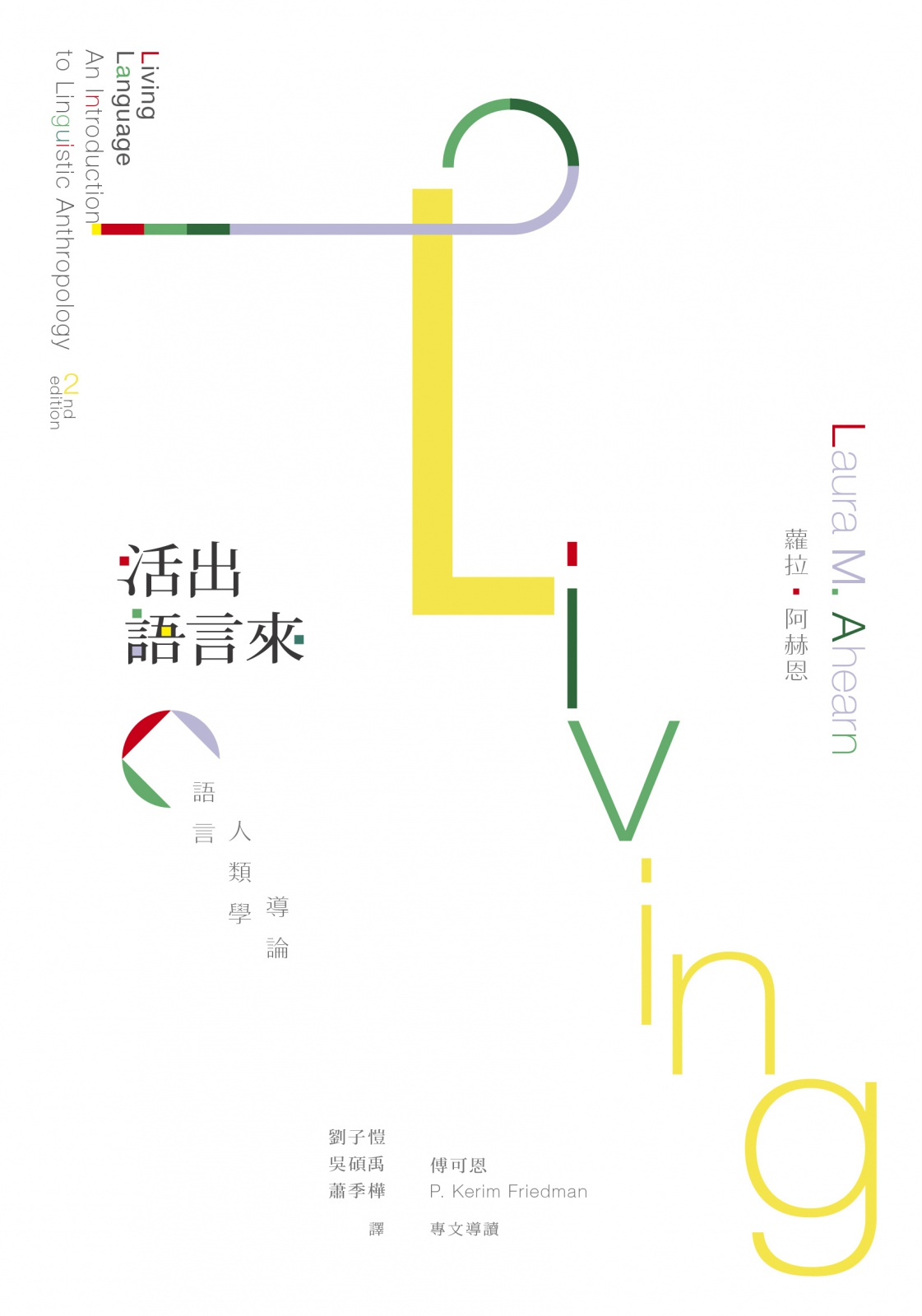
透過選擇使用原住民語的拉丁文字為她的名字,Kolas正試圖改變台灣人與這些符號的關聯性,並可能改變了他們與原住民之間的關係。這樣的語言並不只是引用與既有的人群之間的關聯,而是可以用來試圖改變這些關聯,用於解釋為什麼針對語言使用的爭論,如:關於使用性別化代名詞的辯論(Silverstein 1985),總是遠遠超過語言本身的議題。語言使用的複雜方式可以挑戰和強化既有的組織和規範,這樣的觀點是實踐理論的一部分(這是阿赫恩提出的四個關鍵專有名詞的最後一個)(Ahearn 2017: 25)。隨著臺灣的戒嚴時期在1980年代的終結,以及1990年代放寬對本土語言的限制,臺灣原住民積極爭取使用他們的傳統名稱的權利,但是很少有人這樣做,因為官僚制度上的障礙或他們害怕被歧視。大多數中文名字只有兩個或三個字的長度,即使臺灣在1995年使用原住民族語的名字變為合法之後,許多官方表格並沒有提供額外的填寫空間,用於書寫原住民族語的名字(Gao 2015)。(使用拉丁字母作為原住民名字是在2006年合法化的。)正如Mayaw Biho(馬躍.比吼)的紀錄片《請問蕃名》所記錄的,許多臺灣原住民早期抓住這個機會改變了他們的名字,但後來又將原住族語的名字改回中文名字,因為他們擔心在就業市場上受到歧視(Biho 2004)。在美國進行過的一項研究顯示這種擔憂可能是有確切根據的。美國的社會科學家發現,如果申請者的名字明顯與少數族裔有關,而其他部分相同的履歷,收到「雇主回覆電話的機率會減少30%到50%」(Kang et al. 2016: 2)。如果臺灣原住民對使用他們的傳統名字感到十分自在,那仍將需要針對在地的語言實踐,以及合法化這些實踐的意識形態做出重要改變。阿赫恩在書中提出的語言人類學的核心概念,提供了一套有用的框架,讓我們能透過此架構開始解釋和揭示這些爭論。
語言人類學是一個令人興奮的學門,它正快速發展,在方法論上和理論上,對語言研究和社會科學都有其獨特的貢獻。蘿拉.阿赫恩的書已經出版了第二版,該書是目前最受歡迎、可以理解的和讀起來有趣的語言人類學教科書之一,它有系統且詳細地介紹了這個令人興奮的研究領域。在此學科中,仍沒有一本語言人類學的當代中文翻譯著作,因此這本中文翻譯書是把阿赫恩所介紹的重要概念翻譯成中文的重要里程碑。反觀日本,像是麥可.西爾弗斯坦(Michael Silverstein)的一些英文著作,則於2009年就已被翻成日文(シルヴァスティン2009)。這本中文翻譯書以有系統的方式說明人類學對語言的社會研究的近期貢獻,因此,這本書將是重要翻譯著作之一。而社會語言學、傳播學、媒介研究、論述分析、敘事分析、談話分析(speech analysis)和其他相關領域已在大學課程規劃中佔有一席之地,並成為重要的大學課程學習領域,對於這些領域的學者來說,這本中文翻譯書將能提供寶貴的資源。翻譯這本書的三位老師組成了專業團隊,並可望帶領中文讀者對語言人類學有深入瞭解。我從一開始就關注於這本書的翻譯過程,他們對於原始資料中的細微差別之敏感性,以及他們進行翻譯過程的反思,令我印象深刻。雖然譯者的角色往往是不易被看見的,但語言人類學教導我們應注意到此一事實:語言意義不是透明的,意義可能是與觀眾共同建構的。
因為本書的中文讀者與最初預期的英文讀者是不同的,因此必然會有一些主題需要更多的脈絡知識才能被理解,而不是輕易地以註解或註腳來提供內容說明而已。本書第十一章「語言、種族和族群性」特別是如此,其內容涉及對美國種族關係的一般性背景知識,特別是對西班牙語人士和非裔美國人白話英語(African American Vernacular English, AAVE),也稱為「黑人英語」(Black English 或Ebonics)說話者的背景知識。當我在臺灣的大學課堂中講授這些題材時,我發現我的學生們驚訝地得知,黑人英語曾被當作黑人智力較低的「證明」。奴隸制度的歷史遺產以及美國內戰後施行的種族隔離,導致美國白人製造了許多偽科學理論為這些不人道的政策進行自我辯護。這種完全不科學的做法通常被稱為「科學種族主義」(scientific racism),並試圖證明白人對黑人的統治是合理的,因為黑人像小孩一般,他們在心智上不適合自我管理。黑人英語的獨特語言特徵被用於證明其說話者的心智能力較低。這些語言特徵被認為是較差的心智能力和懶惰所造成的結果,而不是因為黑人英語是一種接觸語言(contact language),它受到奴隸從非洲帶來的非洲語言元素的影響。
很難想像當今社會,會有任何人相信這樣的無稽之談,甚至為了反駁而認真看待這種近乎侮辱的說法。然而,現代社會語言學的創始人之一,威廉.拉波夫(William Labov) 覺得他不得不這麼做,目的是為了挑戰仍盛行於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的教育典範。在他的一篇開創性論文〈非標準英語的邏輯〉(The Logic of Nonstandard English)之中,他試圖挑戰用於解釋黑人兒童於學校中的表現不佳的「文化缺陷」模型,他主張黑人英語與英語的任何其他變體一樣能表達出複雜的邏輯思想(Labov 1972)。正如阿赫恩針對1996年黑人英語爭議(The Ebonics controversy)的討論所指出的(當美國加州奧克蘭的一所學校的董事會試圖將黑人英語作為學校官方課程的一部分之時),許多黑人已經將這種獨特的美國人語言的負面態度加以內化(Ahearn 2017: 230-231)。雖然臺灣沒有類似的奴隸制度或科學種族主義的歷史遺產,但就在不久之前,有些臺灣人認為說河洛語的人是一種沒有受過教育的符號。申大得(Todd Sandel)發表於2003年的一篇論文中,發現由於臺灣的政治局勢的變化,這種對於河洛語(閩南語)的負面態度正在改變,創造出重視在地語言的新語言意識形態,而這種負面態度並不會常反映在人們的實際語言實踐之中。正是因為語言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論的工具可以幫助我們瞭解這些變化,這本中文翻譯書的出版,對於深入瞭解臺灣和世界其他地方不斷發生的複雜變化,正是一個很好的時機點。
※詳細參考書目請見原書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傅可恩(Kerim Friedman) 《活出語言來:語言人類學導論》導讀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801 )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