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門「落番」時代下的婚姻地景
近年來台灣日本殖民時期歷史研究(含文學史與藝術史研究)的知識轉譯成果百花齊放,從面向大眾的知識性讀物、漫畫、戲劇、電視劇,到結合跨領域研究成果與素材的美術館及博物館展覽等,儼然形成一股台灣史熱潮。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這些不同媒介的展示中,關於歷史人物的呈現有更多的私人性,主題也相當多元繽紛,例如:日治時期台籍知識份子的現代思想與自由戀愛觀,及「新女性」的誕生等,著實打開一個重新認識過去的視野。也許正是在台灣史研究欣欣向榮的這一刻,我們應繼續擴展這個回看歷史的視野,例如:關於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初期,與台灣島處於不同政治脈絡的金門的情況。本文將聚焦於金門的一個特殊時期,其中跨國移工、婚姻與現代性產生密切的互動,形塑了當地與跨域的特殊婚姻地景。我將結合歷史文獻、金門女性的口述歷史集、及我個人採集的田野資料,描述「落番」時代下金門的婚姻地景,特別是知識青年與留鄉婦女的婚姻願景與現實人生。
「落番」(luò fān)為閩南語詞彙,是金門人用來描述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初期,大批島上年輕男子前往東南亞(當時所謂的「南洋」)工作賺錢的現象。[1]「番」字體現了漢人本位觀點,對於金門島民來說,東南亞為「番地」,是文明未開的地區,亦是陌生危險的土地。落番現象反映了當時清朝政府與西方殖民帝國之間實力的不對等:英國在1842年中英鴉片戰爭後,迫使清廷開放五口通商(包含與金門鄰近的廈門),並取得香港,將之發展成跨太平洋航線的重要門戶;1860年清廷又敗於英法聯軍,簽訂《北京條約》,正式應允華人出洋。儘管目的地是「番地」,對於地瘠人貧的金門島民來說,落番是個翻轉人生的機會,於是大量男性放手一博,從鄰近的廈門上船,一路前往東南亞的新加坡、馬來西亞與印尼等地,成為「番客」。[2]
金門所屬的福建省及鄰近的廣東省皆是大量男性勞力移出的地區,由於許多移工最後在海外成家定居,成為「華僑」,因此福建及廣東兩省也被稱為「僑鄉」。[3]大批出洋的番客或僑民在海外努力賺錢寄回家鄉,這些匯款被稱為「僑匯」,逐漸成為金門許多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事業有成的番客更是帶動金門當地社會的現代化,從蓋洋樓、鋪路、引進西醫與公衛,到建立學校與推動西方現代教育。本文討論將聚焦於1920到1940年代,這是上述大部分現代化建設出現的時代,也是清廷被推翻及中華民國建立的新體制時期。在此政治經濟劇變的脈絡中,金門島民與番客有了新的婚姻願景,既有的婚姻習俗也被附上了新的意義,新想法與舊制度交會下產生了這時金門特殊的婚姻地景。以下我先說明這些出洋的金門男性是如何結婚的。

不在場的新郎:父母作主的婚姻
漢人在金門定居的歷史久遠,到了明清兩代,好幾個地方宗族已培養多位子孫參與科舉考試並取得功名,其中不乏考取進士者。這反映了金門島民對官方正統儒家文化的深刻吸收,並呈現於宗族聚落中雄偉的家廟與宗祠建築,及莊嚴的祭祖儀式。在兩性關係上,自然也是恪守儒家嚴格的兩性分界,婚姻主要是由雙方父母作主,這也包括在早期台灣常見的「童養媳」婚姻。在20世紀初期大量男性島民落番的情況下,留在原鄉或僑鄉的父母積極為適齡兒子尋找婚配對象,或是以童養媳的方式,先為即將出洋的兒子找好未來的妻子。一位金門的報導人告訴我,他的叔叔在十三歲時前往新加坡工作,而他的祖母在兒子出發之前,為其找了一位童養媳,使其陪伴在自己身邊。等到兒子到達適婚年齡時,這位母親不斷寫信催促兒子回家;在信中,這位不識字的母親,畫下迎娶時做熱鬧的鑼鼓,以告訴兒子趕快回來成親。
中國社會學家陳達於1930年代在福建與廣東僑鄉做的調查,也指出留在原鄉的父母費盡心思為在海外的兒子尋覓原鄉的婚配對象。例如:即便是很貧窮的家庭,也想方設法將兒子的僑匯省下一部分,以供兒子結婚時的聘金與婚禮等開銷。[4]這些男性移工的婚姻雖看似遵循慣例,但父母決定兒子婚姻的權力並非不可挑戰;事實上,在那遠距離通訊極度困難的時代,在原鄉的父母並無法掌握兒子的情況,也時時擔心兒子出洋後就音訊全無。透過為兒子找一位原鄉的妻子,及不斷地催促兒子回鄉成親,或許是許多父母消解焦慮的一種方式,也是期待兒子最終能回鄉延續香火的一種努力。從強調親屬實踐的人類學新親屬研究來說,這些父母為兒子婚事付出的心力,可視為親屬實踐的構成性力量(constitutive power)的展現,[5]以達到傳宗接代這個較保守的繁衍目的;但稍後我也會指出,這個構成性力量也可能啟動改變,以培養能面對新環境的下一代。
大量落番的年輕男子不只是引發其父母的焦慮,也顯著衝擊了僑鄉的婚姻市場。進入20世紀之後,愈來愈多金門家庭仰賴僑匯的挹注,及期待番客回鄉時帶回來的大批禮物;在海外建立起大事業的人,更在家鄉建造融合中西方建築特色的宏偉洋樓。這些物質性的感官衝擊,誘發了身在僑鄉的人的想像,強化了落番與賺取財富的連結,使得僑民成為婚姻市場上熱門的婚配人選。在一份由金門珠山薛氏宗族所發行,讓海外僑民能與僑鄉鄉親保持聯繫的僑刊《顯影》中,可見許多相關的記事。[6]例如:有一則記事寫道:「永昭自送腊歸來,則譜求凰之曲,引得蝶使蜂媒,盡量介紹。其中燕瘦環肥、學生閨秀,計有卅二位,美不勝收。」[7]不只是許多父母紛紛透過媒人,將自家女兒介紹給海外歸來的僑民,年輕女性可能也認為僑民是理想的結婚對象。一位金門的許女士表示自己雖是在父母作主下,嫁給在新加坡工作的番客,但她自承:「我像瞎子一樣,也沒看對方是瘸腳還是半遂,還歡喜嫁個番客」,因為「那時這裡的人都認為嫁個番客是一件很好的事」。[8]

然而,這種「歡喜嫁個番客」的熱潮卻導致無數令人不勝唏噓的婚姻故事。大部分的番客不會攜家帶眷落番,多是將新婚妻子留在家鄉照顧父母,因此許多女性從完婚的後一刻起,就與丈夫維持著遠距離婚姻,甚至可能永遠等不到丈夫回家。金門有句諺語「十去六亡三在一回頭」,描述當時番客出洋的可能下場:十位落番,六位客死異鄉,三位留在異鄉,最終只有一位回到家鄉。留在家鄉的番客妻子不僅可能面對前述情況,也可能遇到丈夫在異地另結新歡並建立家庭。稍後我會回來討論這些留鄉婦女的婚後生活與倫理掙扎。
知識青年的婚姻改革
先前提到的僑刊《顯影》,其創刊的1928年,正是許多金門番客在海外取得成功,將大筆僑匯投入原鄉現代化建設的時候;《顯影》本身既是這股現代化的成果,亦作為繼續推動金門邁向一個現代社會的推手。《顯影》的編輯及提供文章的作者,多為身在金門或海外的珠山薛氏宗族的年輕男性子孫,在海外或鄰近的廈門接受西方現代教育,其中有些人任教於以僑匯建立的珠山小學。在《顯影》發表的各類型文章中,皆可見這些男性作者呼應中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批評父權及傳統婚姻制度,並提倡男女平等、婦女解放、以自由戀愛為基礎的婚姻。例如:《顯影》的第一任編輯施伍(此為筆名),在一篇名為〈五年來的金門婦女〉中,提出《顯影》創刊五年來,他對金門當地婦女問題的觀察,以犀利的筆調抨擊僑匯經濟對於金門社會的腐蝕:「這幾十年來的金門社會,因為南洋華僑資本的輸入,帝國資本主義的壓迫,農村社會受其影響,日趨崩潰。婦女在男子的眼光裡變成為玩物,華僑的家庭多娶一個婦女,便是多得一個家妓。」[9]他也惋惜五四運動的精神未能深刻影響金門,因為:「[在]農村經濟崩潰的金門,家長送他們女子到學校去,既然是投機的指使,那麼最大的目標也脫不了是要提高女子的價值,利用將來在婚姻買賣上多賺一分的利潤。」[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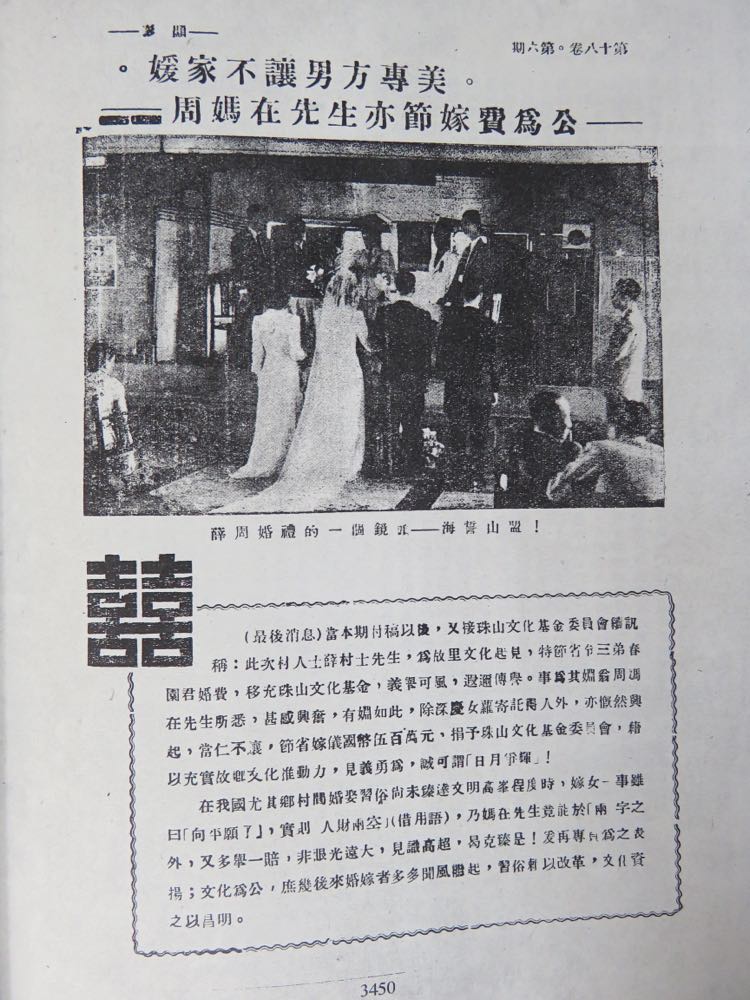
另一位身在東南亞,筆名為鏡心的作者,在〈關於婚姻底儀式的我見〉中,批評傳統婚姻儀式,包括媒婆說合、父母作主、及迎娶和大鼓吹等儀式為「半開化」,只是「無謂的喧鬧」;認為「夫妻相處,其合作力到什麼田地,要看他們的戀愛澈底不澈底做標準。假使沒有心意一致的愛做他們的樞紐,他們的婚姻的儀式無論多麼隆重,就是請制禮的周公做他們底證婚人,也買不到他們底真夫妻心!」[11]然而,儘管這些知識青年為文批評父權體系與傳統婚姻儀式,也難以撼動其他島民去推翻長久以來的父系價值與文化慣習。靜心的文章最後祝賀施伍即將結婚,後者以另一個筆名伶彥回覆靜心的提問,文中透露自己已無法保持革命的精神,只能「盡量去適合環境,拜服於舊禮教之下」。然而,作為最後的一點抵抗,施伍表示自己將離開家鄉前往新加坡,既是為了生計,也是「十分的希望早日離開這個死路的閩南」。[12]
從《顯影》的其他新聞中,可知施伍的結婚對象是一位在金門任教的小學教師,兩人「初為學問之切磋,經過精細的審查,以為可作終身伴侶」,且他們採取「同居」而非傳統的結婚儀式。[13]這裡的「同居」,並非現在所謂的有戀愛關係的兩人同住,不論是否最後會結婚。對照《顯影》的其他新聞可發現,「同居」就是事實婚,是當時不少知識分子採取的方式,強調婚姻是兩人自主決定,並且不採用任何傳統、複雜的結婚儀式。換言之,儘管施伍自承無法推翻「舊禮教」,其個人仍是親身實踐了新的兩性觀念與婚姻締結方式,這也反映了當時許多知識份子親身示範新觀念與新作法,以號召追隨者。
改革論述中被忽略的親屬角色
上述《顯影》中的幾個例子,一方面呈現僑匯經濟與婚姻慣俗互動下產生的問題,另一方面顯示知識青年將婚姻改革視為建立現代中國的重要基礎。這些知識青年的論述不斷地強化傳統父權體制與現代文明之間的對立,藉此強調前者的落後及「傳統家庭與婚姻」所造成的男女不平等,主張應以重視個體自主性和性別平等的現代文明來取代之。如此論調把婚姻予以政治化為一個關乎國家未來的議題,同時也把重視延續父系的漢人親屬與家庭形塑為一個保守反動的角色。然而,根據人類學的新親屬研究,我們可以透過探究親屬實踐(kinship practices)或親屬的構成性力量,以重新思考漢人親屬與家庭如何可能扮演一個推動改變的角色。
美國人類學者Sylvia Yanagisako便是從親屬實踐的角度,來研究義大利傳統的家族企業如何藉由自我轉型成跨國公司,以在當今高度競爭的全球市場生存下來。[14]她在討論家族企業中的世代間(intergenerational)傳承時,特別強調generation的另一個英文含義,也就是creation,創造,目的是跳脫從一個生物性繁衍的模式來研究這些家族企業的維繫。她認為應將這些家族企業視為kinship enterprises(暫譯為「以親屬為基礎的創新企業」),這些企業是透過一而再、再而三地檢視與調整自己的目標與策略,亦即保持自我轉型的能力,來維持生命力。這種轉型的過程包含將子孫送去學習企業與財務管理、資訊科技、行銷與經濟等專業,而能不斷吸納整合最新的管理技術與組織形式於家族企業之中,進而熔鑄出一種現代家族資本主義,並以新的公司汰換舊的公司以持續壯大自身。
這種強調自我轉型能力的親屬實踐邏輯其實也可在漢人親屬中發現,落番時代下的金門家庭便力行此邏輯:賺了錢的番客會讓孩子,尤其是兒子,去接受西方現代教育,繼續推進整個家族的向上社會流動;也會以傳統的媒人說合、父母作主的方式,為子女尋找社經地位相當的對象,藉由締結有力的姻親來強化家族事業。更重要的是,這種自我轉型的親屬實踐邏輯不只是圖謀家族自身的壯大,也可能推進社會的改變。例如: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自金門撤退後復刊的《顯影》中,有一篇新聞提到一位僑民將自己結婚時收到的禮金捐出,交由《顯影》的編輯們去為家鄉的孩子們添購兒童讀物。[15]之後,《顯影》的編輯們為了籌措辦雜誌的錢,公開於雜誌中鼓勵僑民們可將結婚禮金捐給雜誌社,而這也確實得到不少新婚僑民們的響應。這些捐贈的禮金不只是用來維持雜誌的發行,也用在維持珠山小學的營運。換言之,即便結婚禮金是屬於傳統儀式的一部分,但其可以用在創造性的目的上。辦雜誌與興學是為了推動金門社會的現代化,及培育下一代面對新的時代與環境,而這些是奠基在親屬網絡與實踐上。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在當時自我轉型的親屬實踐中,仍有濃厚的父權思想與性別不平等,女性接受教育並透過教育建立獨立自主人生的機會依然很少,許多嫁給番客的女性更是在沈重的社會壓力下過著終身守節的生活。
留守父系家庭的番客妻
「[我們是]相欠債(閩南語)」,一位1940年代嫁給番客,我稱之為蘇婆婆的女性如此描述她與丈夫的關係。蘇婆婆當時也是在父親作主下嫁給同村的一位男性;即便是同村,因嚴格的兩性分界,蘇婆婆自述婚前沒怎麼見過先生,對其一點兒都不了解。婚後一年,當蘇婆婆即將臨盆的時候,其先生突然決定出洋到新加坡工作,豈料自此一去不回。我從蘇婆婆的兒子口中得知,當時新加坡被日軍佔領,他的父親有參與華僑的抗日運動,似乎在一次活動中遇害身亡。20歲出頭就成為寡婦,育有尚在襁褓中的兒子的蘇婆婆,只能一肩扛起養家的責任,在鄰人的田裡幫忙較粗重的農務,勉強維持母子兩人的溫飽。一路艱苦地走來,關於我問起她那早逝的丈夫,蘇婆婆搖搖頭,只以「相欠債」來總結與丈夫的關係。
落番時代下的金門,大部分已婚的番客或是出洋後回鄉成親的番客,仍是隻身下南洋,將妻子留在家鄉照顧父母與子女。類似的情況在同屬僑鄉的廣東與福建兩省亦相當普遍,這種異地婚姻被認為是傳統漢人「男主外,女主內」性別分工的產物。此外,因許多番客起初並無定居海外的想法,分居兩地亦是暫時不得已的安排。有歷史學者借用人類學漢人親屬研究的觀點,亦即把漢人的「家」視為一個共有財產的集體(a corporate property-holding unit)[16],將這種分居家庭視為一種極大化家族的共同經濟利益的策略,因為留鄉婦女擔任管理家產(包含以僑匯投資的新資產)的重要角色。[17]然而,大多數需落番的金門家庭本身沒有什麼資產,而落番內含「十去六亡三在一回頭」的高度風險,許多番客在能匯錢回家之前便已葬身異地,或是賺不到錢寄回家鄉;許多留鄉婦女只能像蘇婆婆這般,一肩扛起家計。此外,從經濟利益的角度來分析落番時代下的分居家庭,容易忽略了這些番客與留鄉婦女的非工具性動機、情感與倫理。

雖然金門番客大多是隻身出洋,有些人還是攢了一些積蓄並回鄉接父母妻小到南洋。金門一位蘇洪女士在口述歷史中,提到自己在馬來西亞工作的丈夫曾經回鄉要接她、幼小的女兒與父母到南洋,然而這位丈夫當時已在異地再娶,對象是來自大陸的女性,曾在這位先生重病時悉心照顧之。[18]蘇洪女士最後回絕了丈夫,因為公婆年事已高,不便一起遠渡重洋,但她又不放心留老人家在家鄉;另一方面,她也擔心丈夫無法同時贍養兩個家庭。蘇洪女士的丈夫再度前往馬來西亞後,兩人餘生未再相聚;倒是這位丈夫從南洋寄了一台針車(縫紉機)回來,蘇洪女士與大娘姑和嫂嫂利用這台針車做起縫製及修補衣物的生意,養活一家老小。蘇洪女士的故事顯示了番客與留鄉婦女的情感與倫理掙扎:出洋後另娶妻子的番客丈夫並未遺忘自己家鄉的父母與元配妻子;留在家鄉的妻子同情同樣留鄉的公婆與顧慮丈夫的經濟負擔,選擇留在夫家,成為家庭的經濟與精神支柱。
終身守節的留鄉婦女
去過金門的遊客,可能看過後浦老街上一座雄偉的「邱良功母節孝坊」,[19]它是清代金門出身的浙江總督邱良功,因感念守寡並養育他的母親,向清仁宗上表懇請旌獎,經皇帝准允後建造的貞節牌坊。貞節牌坊反映了官方正統的儒家價值,強調女性婚前與婚後的貞潔,丈夫逝世後再婚是被道德譴責的選項;政府並以旌表來鼓勵女性守節,例如:准予建造貞節牌坊,而在許多仕紳文人留下的文獻中亦有「節女」與「烈女」的記事。清末貢生林焜熿編撰的《金門志》,紀錄了不少清末「節女」與「烈女」事蹟,包括上述邱良功的母親。民國十年出版的《金門縣志》,也有不少丈夫客死南洋的留鄉婦女終身守節的記錄。換言之,即便五四新文化運動已進行了數年,傳統的貞節觀念在金門社會依舊聞風不動。有一位教師退休的金門報導人告訴我,如果現在還有旌表制度的話,現任總統應該為仍在世的,為客死異鄉的丈夫守節的留鄉婦女設立貞節牌坊。
雖然當時貞潔觀念確實是構成許多女性道德人觀(personhood)的重要面向,但若直接將留鄉婦女的終身守節類比到過去的節女典範,也許未能貼近理解這些女性的主體情感。我試著從人類學家Veena Das的日常倫理(ordinary ethics)概念,[20]來探究這些留鄉婦女可能有的複雜情感與倫理掙扎。在Das的討論中,日常倫理並非是人們與日常行為保持一段距離所做的評判(judgements),而是將倫理理解成瀰漫於一個人的整體生活之中。其中,所謂的日常(the ordinary or the everyday)不只是日復一日進行的活動、慣習或符合社會常規的行為,而是包含了猜疑、不安、虛幻、不尋常經驗的各種可能性;能夠度過每一天的生活本身便構成一種成就,因為「度過每一天」可能需要一點創新、需要能隨機應變、需要經歷一番倫理掙扎才能達成。Das對於日常倫理的見解深具啟發性,有助於更加貼近理解金門落番時代下,留鄉婦女的主體情感及她們如何努力地把每一天過下去。
前面提過蘇婆婆將自己與番客丈夫的關係描述為「相欠債」,包含了憤恨不平又只能無奈接受現實的情緒,而非僅是如地方誌中對於節女的描述:「矢志」或「甘心」守節。另一位嫁給番客的王女士說道:「丈夫一去南洋,幾乎沒和我聯絡,算是沒有真情意」,而且「婆婆有時不是對我很好,但想到婆婆二十八歲就守寡,我一離開,婆婆就會孤單一個;又想到我的娘家是有名聲的人,我就一心一意把獨子養大,就是我的希望了」。」[21]由於王女士的丈夫在海外另建家庭,很少捎來音訊與僑匯,王女士只能靠做女工來養活自己、婆婆與兒子。在她的自述中,她的終身守節並不是出自對丈夫的感情或是完全服膺於傳統貞潔觀念,而是包含了對於婆婆的同理心,對於娘家聲望的在意,以及將養育獨子作為生活下去的動力;一手帶大兒子的蘇婆婆也是如此。根據Das對於日常倫理的討論,蘇婆婆和王女士的倫理實踐並非僅是恪守傳統上對於女性貞潔的期待,而是即便因丈夫的缺席而可能有憤恨、不滿或無奈、悲傷的情緒,仍努力讓自己的行為與生活方式可以不悖於社會常規與自我道德人觀,並透過與自己所關心之人的連結,讓自己可以克服每一天艱困的生活,並建構自己的道德主體性。
結語
本文以簡短的篇幅嘗試從多元主體的立場來描述金門落番時代下的婚姻地景,及其中跨國移工、僑匯、現代性、傳統漢人親屬與倫理之間的交會互動。對於當時兒子落番的許多父母而言,為兒子決定結婚對象及安排婚禮,也許不只是傳統父母權威的展現,更反映了父母對於兒子的長期缺席甚至再也不回故土的一種焦慮。因僑匯刺激了落番與財富的連結,許多育有女兒的金門父母及年輕女性本身,皆認為番客是理想的婚配人選。受惠於僑匯經濟而接受西方現代教育的知識青年,則大力批判傳統婚姻制度與「嫁番客」的婚姻潮流,提倡男女平等、自由戀愛與婚姻自主權;但在其犀利的批判中也過度強調傳統漢人家庭與現代文明的二元對立,而忽略了親屬實踐(例如:對於後代的教育投資)其實是促進社會改變的一股基礎力量。落番的高度風險與「嫁番客」的風潮交織下導致了許多終身守節的留鄉婦女,她們或許在社會壓力下並沒有什麼選擇空間,但她們不僅僅是「矢志」或「甘心」遵從社會期待,而是在五味雜陳的情緒中,努力地扛起家計、照顧公婆與孩子、保持自己的貞潔,透過努力地活過每一天來建立自己的道德主體性。落番時代下的金門,是一個傳統與現代不同思想與價值並陳、交會與衝突的場域,生活在其中的人可能因落番、僑匯、婚姻等產生各種不同的連結,而也有各自不同的人生。
[2] 雖然大部分的金門島民是前往東南亞,也有部分島民前往日本的長崎與神戶。
[3] 見:江柏煒,2004。《閩粵僑鄉的社會與文化變遷》。金門: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陳達,2011[1939]。《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
[4] 陳達,2011[1939]。
[5] McKinnon, Susan and Fenella Cannell (eds). 2013. Vital Relations: Modernity and the Persistent Life of Kinship. Santa Fe, NM: SAR Press.
[6] 僑刊或鄉訊一般是由海外僑民募款支助,由家鄉的知識份子來編撰,印刷後於分發於僑鄉及海外各僑居地。也因此,僑刊或鄉訊的內容多是報導僑鄉的各種新聞,特別是有關親族的動態,所以有許多訂婚與結婚的消息。金門曾有多個宗族發行僑刊,但完整保存至今的只剩《顯影》(創刊於1928年,於1937-1945年間因日軍佔領金門而停刊,1946年復刊,持續發行至1949年古寧頭戰爭爆發為止)。見:江柏煒,2005。〈僑刊史料中的金門(1920s-40s):珠山《顯影》(Shining)之考察〉,《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17卷1期,頁159 – 216。
[7] 《顯影》,2006。金門:國立金門技術學院,頁1760。
[8] 劉湘金,2006,《浮繪僑眷家庭婦女的生活圖像:探討金門地區1930-1950僑眷家庭婦女的角色與功能》,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碩士論文,頁118。
[9] 《顯影》,2006,頁1626。
[10] 《顯影》,2006,頁1627。
[11] 《顯影》,2006,頁2041-2045。
[12] 《顯影》,2006,頁2045-2046。
[13] 《顯影》,2006,頁1847, 2021-2022。
[14] Yanagisako, Sylvia. 2013. ‘Transnational Family Capitalism’, in Susan McKinnon and Fenella Cannell (eds), Vital Relations: Modernity and the Persistent Life of Kinship. Santa Fe, NM: SAR Press, pp. 74–95; 2019. ‘On Generation’, in Lisa Rofel and Sylvia Yanagisako, Fabricating Transnational Capitalism: A Collaborative Ethnography of Italian-Chinese Global Fash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 228–63.
[15] 《顯影》,2006,頁3220。
[16] Cohen, Myron L. 1976. 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The Chinese Family in Taiw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7] Mazumdar, Sucheta. 2003. ‘What Happened to the Women? Chinese and Indian Male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Global Perspective’, in Shirley Hune and Gail Nomura (eds), Asia/Pacific Islander American Women: A Historical Antholog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pp. 58–74; Szonyi, Michael. 2005. ‘Mothers, Sons and Lovers: Fidelity and Frugality in the Overseas Chinese Divided Family Before 1949’,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1(1): 43–64.
[18] 劉湘金,2006,頁113-115。
[20] Das, Veena. 2007. Life and Words: Violence and the Descent into the Ordinary. Berkeley, CA;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Ordinary Ethics’, in Didier Fassin (ed.), A Companion to Moral Anthropology. Chichester;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pp. 133–49; 2018. ‘Ethics, Self-Knowledge, and Life Taken As A Whole’,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8(3): 537–49.
[21] 劉湘金,2006,頁109-112。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邱筱喬 金門「落番」時代下的婚姻地景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985 )



回應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資料豐富是沒錯,但寫法在這種公共平台(非學術期刊)不是那麼流暢吸引人讀下去,很有距離感,尤其是非學術的和新讀者。
無論如何,是篇好文。
文中很多段的口述歷史都勾引出許多畫面,其中印象深刻的,是在當年的時代背景之下,構成了男性遠渡重洋落番,女性在家鄉獨守空閨,獨自持家育兒、照顧公婆的意象,回映到台灣早年,1990年代大量台商西進大陸投資經商,後來在大陸另組家庭,或是客死異鄉,或是在對岸就此落地生根,甚至是撤退(逃)回台灣的故事,都屢見不鮮,兩種不同的時代背景下,故事脈絡卻有著巧妙的雷同,是我認為相當有趣的部份。
另外,在貞節牌坊的部分,也感受到華人女性,在儒家思想影響下的社會氛圍,丈夫外出工作或在外另組家庭,甚至客死異鄉,都需要持守貞潔,以專心致志的照顧家庭,回應鄰里社會的期待,建立起給別人探聽的名聲。女性在這樣長期壓抑情感及內在需求的環境下生活,其實是相當不健康的,情緒狀態也容易不太穩定,因此不利於自我的照顧或子女的教養,這部分就不知道有沒有金門落番下一代的相關文獻資料了,因為我對於受壓迫女性的下一代的身心健康相關影響有些興趣。
感謝筱喬老師的分享。
作為我這個在金門長大的新金門人還說雖然這些是離我有一段時間距離的故事,不過蠻能夠想像那些作為番客妻的女性處境,據我之前在金門聽到的類似情況中甚至有些女性是沒有生育就與丈夫分隔兩地沒有再見面的也有,但這些女性也沒有改嫁仍是持續事奉公婆至其晚年,真的很佩服當時的女性。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