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與人類學知識
談越戰中的人類學家身影
剛開學的一個週五晚上,我服務系所的退休美國老教授約吃飯談事情,酒酣耳熱之際,我突然脫口一問:「這也許聽起來是個天外飛來一筆的問題‧‧‧越戰的時候,你在哪裡?」愣了一下,認可這確實是天外飛來的一筆,他表示自己當時在大學唸書,沒有被徵召,但認識很多參戰的朋友,其中不少就這樣死在異鄉。如同當時許許多多的年輕人,他非常痛恨這場戰爭,也參加了反戰遊行。「你知道那時候發明『教學抗議』(teach-in)活動的,正是人類學家Marshall Sahlins嗎?」他說道。是的,我當然知道。人類學家怎麼可能會在這牽連層次如此之廣的事件中缺席呢?在接下來的文章中我將談兩位越戰中的人類學家,以及他們對人類學知識不同的定位。但在此之前,請容我解釋一下我的唐突一問。
《越戰》紀錄片
在稍早瘟疫蔓延的寒假中,我窩在家裡把美國知名歷史紀錄片導演Ken Burns和Lynn Novick耗時10年完成的長篇史詩、共10集18個小時的《越戰》(The Vietnam War,2017)紀錄片系列追完,心情久久難以平復。這場即將在4月30日於越南慶祝其終結45週年的戰爭,是美國國際軍事行動史上最大的挫敗,造成5萬8千多人員身亡,超過30萬人受到各種不同身軀的傷殘,這還不包括因此役而正式診斷出來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患者。另外方面,戰爭期間反戰、民權、女權等運動風起雲湧,伴隨著國內與國際政局的動盪、角力、暗殺、醜聞,使得美國渡過南北戰爭後最為對立分裂的一段時間。而終於完成統一大業的越南也蒙受空前損害。根據估計,包括南北越正規軍、越共游擊隊、全境平民的死亡人數超過200萬人。至於美軍投下的各式炸彈、導彈、燃燒彈(總量為二戰的三倍之多)以及惡名昭彰的枯葉劑,至今仍持續影響著環境與居民健康。
Burns和Novick的《越戰》透過檔案、訪談和越戰另一項革命:可觀的戰地新聞畫面,從1858年法國在中南半島的殖民講起、到1982華府越戰紀念碑的建造以及當代美越雙方的和解交流,鉅細靡遺地交代了這場時代的悲劇。其最具突破性之處在於納入越南在地聲音,採用大量前南北越軍人、越共游擊隊員的越南話訪談,使在主流論述和再現中總是面目模糊的他者,有了名字、面孔、和同樣深刻的傷痛故事。《越戰》在播映後獲得極高的評價,但也受到來自左右兩邊的批評。一些南越和美軍軍人覺得其犧牲貢獻被重點放在勝利方北越和反戰的論調淹沒;另有一批美軍軍人和學者則認為紀錄片為美國帝國主義開脫,沒有針對背後的全球政治經濟框架進行足夠的批判,更別提對戰爭真正的反省。歷史學家Thomas Bass的影評指出,紀錄片一開始那句「一場本意良善的戰爭」就不正確,之後將之定調為南北越「內戰」的說法更是不當。南越是法國殖民主義的發明遺留、在美帝扶植下成立的政權,這場戰爭的本質是徹底的越南獨立之戰。
Bass認為《越戰》紀錄片中的「內戰說」是受到一位越南主要訪談人Duong Van Mai(在《越南:世界史的失語者》一書中音譯為楊文美)的影響。楊女士生長於河內的中產階級家庭中,父親是法國殖民政府的官員。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姐姐和兩個哥哥加入胡志明領導的越盟,反共的父親則帶著全家遷往西貢,因此越戰爆發時,她有很強烈的分裂感。她另外一個重要的身份是知名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職員,在西貢擔任越共戰俘訪談的翻譯,之後與同樣曾為蘭德工作的美國政治學教授David Elliot成婚,搬到美國居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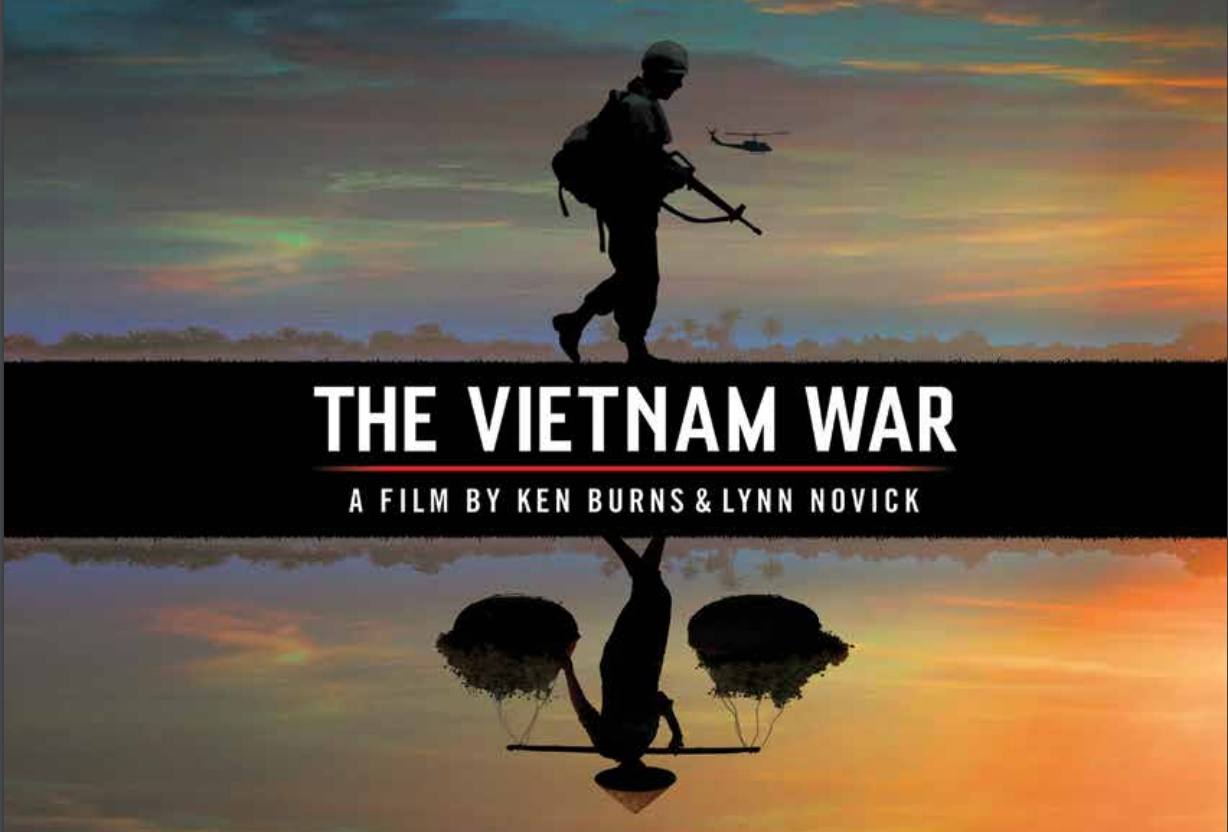
與軍方攜手的人類學家
成立於1948年的蘭德最主要的服務對象為美國軍方,透過研究提供政策上的建議,特別是在太空競賽與核武的項目上,包括三十多位諾貝爾獎得主(多在經濟學領域)以及人類學家Margaret Mead都曾與之合作。蘭德於1950年代開始對中南半島政治局勢進行調查,持續追蹤越共游擊隊的行動和戰略。美軍正式參戰時,當時國防部長Robert McNamara(自身也是一位賽局理論信徒)深受其分析報告的影響。有意思的是,蘭德第一位派遣到越南的研究員就是一位人類學家:Gerald Hickey。
1959年在芝加哥大學拿到人類學學位的Hickey博論田野地就是湄公河流域的越南村落,在田野期間也已經與中央情報局人員接觸,協助規劃西貢政府公職人員的訓練。畢業後則持續為政府和福特基金會在越南的計畫案擔任顧問。1961年,在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ARPA,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的經費補助下,他代表蘭德準備前往越南中央高地進行被法國殖民政府稱為「高地族」(Montagnard)的研究,企圖瞭解他們希冀的事物為何,南越政府如何能「贏得他們的心」。然而,由於戰事逐漸升溫無法進入中央高地,他只能更換題目,研究美軍「戰略村落計畫」(Strategic Hamlet Program)的推行。此計畫將越共勢力範圍中的村民遷到擁有防禦工事的「戰略村落」中居住,藉此切斷他們與越共的聯繫,並同時設立哨站、宵禁、識別卡、劃出「禁區」。Hickey透過訪談發現村民普遍對強迫遷居的狀況感到不滿,額外的勞力付出與生計的損失也沒有得到合理的補償。他將這些負面意見寫進了1962年自己的第一份蘭德報告書中,但並沒有得到執著於以意識形態區分敵我的軍方的重視。
1964年,Hickey又得到一筆ARPA補助金終於得以進入中央高地展開為期十個月的田野調查,並針對族群組成、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合作等主題發表了幾篇報告書,其成果最後集結在《破碎的世界:越南中央高地族群在越戰期間的適應和生存之道》(Shattered World: Adaptation and Survival Among Vietnam's Highland Peoples During the Vietnam War,1993)一書中。這本少見的戰地民族誌指出中央高地包括南島語族的複雜族群內涵。這些族群各自有著不同程度回應變動局勢的策略,而宗教宇宙觀在此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戰爭使得村民流離失所、即使較為安全的聚落也被迫得收容難民,加上其處於深山森林中的生態環境成為美軍枯葉劑噴灑的重點目標,嚴重影響其生計與性命安全。戰爭結束後,約一百萬的高地人口中有五分之一死在這「破碎的世界」中。事實上,他自己也差點命喪於此。田野期間的某個午夜,他在美軍位於南東縣村落的基地中遭遇越共游擊隊和北越正規軍的夾擊,儘管被手榴彈炸飛撞牆,他還是手持AR15步槍作戰,直到敵軍撤退。最後雙方總共有250人身亡,而他的田野筆記與資料也同樣損失慘重。
除了高地田野調查外,Hickey也以西貢為田野地研究了美軍顧問與南越軍方之間的關係。他發現雙方有著顯著溝通與理解上的斷裂,並建議加強美軍顧問的越南語言文化訓練、延長任期、建立經驗分享與延續機制、減低繁瑣的行政工作。他甚至提議共食與同宿來增進情誼。這份在1965年發表的報告書受到越戰美軍總司令Westmoreland上將的高度肯定,但如同之前的建言一樣,沒有任何實質的改變發生。
將社會科學家帶入當代美軍軍事行動的「人類地形系統」計畫主腦人類學家Montgomery McFate,在最新專書《軍事人類學》(Military Anthropology,2018)中相當為Hickey抱屈。她認為他最重要的洞見為「戰爭是軍方與戰地居民的互動過程。若想要順利執行任務,軍方決策需要將當地社會視為整體、納入考量。」但美軍始終沒有理解這點,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冷戰人類學》(Cold War Anthropology,2016)的作者專家David Price則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在讀完所有的蘭德報告書後,他認為Hickey雖有減少戰地居民受害的用意,但這通常是放在軍事利益的框架思考。他甚至對當地社會文化材料的呈現有時隱含著戰略的企圖,使軍方能夠採取相關的行動,例如徵召在地反共民兵,或利用社會組織建立情報網路,反而增加了當地人受害的風險,這是他從未認真面對的倫理議題與人類學知識的政治意涵。正是如此,當Hickey於越戰結束後想要回美國學界工作時,受到反戰立場明確的美國人類學界冷漠的回應。
越戰中人類學家的養成
當Hickey在越南進行田野調查、撰寫報告書之際,1966-67年間有一位高中輟學、才剛滿17歲就主動從軍被送到越南戰場的小伙子,在北部灣海域上的航空站服役,不時搭乘E1-B預警機在越南上空操作維修雷達設備。他是Glenn Petersen,日後將在哥倫比亞大學拿到人類學博士學位。留著兩撇濃密八字鬍的Glenn是我相當敬重的太平洋研究老前輩,跟他也有幾面之緣。對於越戰,他的感覺是憤怒、苦澀、悔恨、被國家背叛。他說他還無法原諒那個參與一場不義之戰的小伙子。1971年,他與700多位越戰退伍軍人在國會大廈前面拋擲丟棄他們在越戰獲得的勳章,這個沈痛控訴的場景在《越戰》紀錄片中也有出現。
在一篇標題為〈如何做個人類學家〉的文章中,他說他很有可能會終其一生陷在悲痛之中,但是人類學拉了他一把,教導他耐心與想像力。在受訓時他在基地圖書館中接觸到一本人類學家Oliver La Farge的創作故事集,裡面描寫了人類學家在不同文化情境中與當地人的互動以及互動之後的後果。從此,他天真地立志也要前往「化外之地」體驗這種生活。他夢想中的「化外之地」之後成了田野地密克羅尼西亞的波納佩島,他的任務也從在戰場中維持偵察雷達順利運作,轉變為在美國政府與島民領袖間,協調密克羅尼西亞聯邦獨立地位的獲致。
或許是因為在越戰時見證到再微小的消息、情報都可能造成巨大的生靈塗炭,以及La Farge那本小說的啟發,Glenn說他領悟到「對我們自己的研究和生涯越有幫助的資訊,越有可能危害到提供這些資訊的群體。」在權力關係高度不對等的研究中更是如此,例如越戰中的戰地田野調查,或當時仍處於美國帝國勢力下的密克羅尼西亞。當地親屬關係與階序制度等資訊雖然看似是中性的人類學知識,還是有可能被美國政府用來影響獨立條件的談判。由於Glenn的謹慎以及對權力關係的敏銳,他一方面得到了島上傳統領袖的信任,另一方面也能以此為基礎將人類學知識合理應用在國際政治協商上。Hickey同樣是一位出色的人類學家與田野工作者,但缺乏對軍事行動暴力本質和權力位置的理解,也因此,他的蘭德報告書不但沒有在越戰期間引起實質效果,也保護不了當地族群持續地受到戰爭的傷害。這也許反映了戰爭與人類學知識的關係,恐怕永遠沒有合作的空間。後者必須時時刻刻處在批判前者的立場上。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林浩立 戰爭與人類學知識:談越戰中的人類學家身影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index.php/article/6809 )




回應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又是美國中心的論調,反感。美國生產的知識就是「棒」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