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座城市成為治療室
—《聆聽的類屬》的自由聯想
這篇文章源自於今年六月受到政大民族所的讀書會邀請,與任教於Emory University西班牙語與葡萄牙語系的人類學家Dr Xochitl Marsilli-Vargas對談她最新出版的著作,Genre of Listening: An Ethnography of Psychoanalysis in Buenos Aires(或許書名就暫時翻成《聆聽的類屬:布宜諾艾利斯的精神分析民族誌》)(註一)。這本書是一本相當特別的語言/醫療人類學作品,它不像是探究傳統儀式的民俗醫療,也不只是批判醫療人類學中對政治經濟大聲疾呼,而是探討一個可以說是一種在擁抱現代性的前提下,在近代都市社會所發展出來的治療文化。
精神分析在阿根廷廣受歡迎,尤其在布宜諾艾利斯(Buenos Aires)這個城市更是發揮到蓬勃極致。有些政治工作者或候選人甚至都會標榜自己有被分析過,彷彿是一種社會資本一般。在台灣,主流的精神醫療的跟精神分析早已拉開一段距離,縱使有相對少數的工作者仍持續進行組織推廣,但畢竟常規的醫療體系的並不提供精神分析的服務,因此當你閱讀《聆聽的類屬》一書,必然會對何以精神分析能在一個特定城市裡蔚為風尚感到好奇。這篇文章將六月期間所進行的兩次線上討論進行一次整理與改寫,文章並非只有針對介紹這本書,卻也算是某種借題發揮,藉以重新想像精神分析與人類學的關聯,並且思索特定治療的大眾化與其歷史脈絡的關係。(註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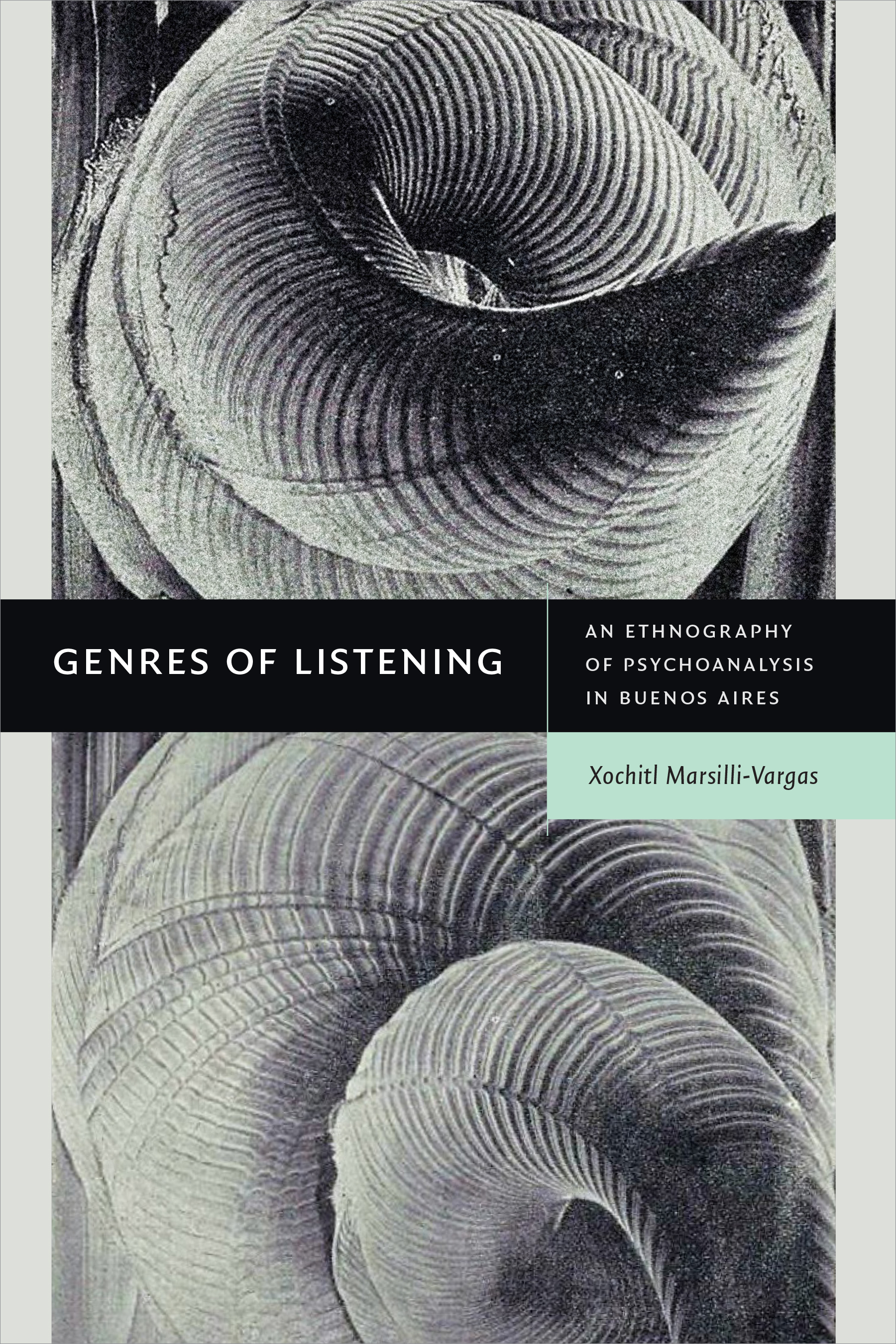
圖一:Genre of Listening: An Ethnography of Psychoanalysis in Buenos Aires 封面
人類學與精神分析的分合
作為研究「人」的學門,人類學與精神分析都被當作探究人類心理狀態的方法之一,它們或許有許多相似性,也有一些不同之處。從細節來說,若以人類學的角度來理解人類的心理狀態,大抵是關切心理健康和疾病與文化變遷的關聯,並且較著重於個體和社會之間的界面;又或者能夠嘗試記錄從個人經驗到文化和社會的敘事,以及關於疾病的治理等等。至於精神分析,則是較著重在人的內在變異,聚焦在個體的意義和經驗,或嘗試捕捉環境適應和個人自由之間的張力。在方法學上,這兩個領域都企圖在一某種既是超然客觀,但又能在實際參與和情感投入之間提問。
人類學家和精神分析師在許多方面當然是不同的,但兩者都致力於探究人類行為和經驗,他們都有自己對所要達到的預設目標以及觀念;換言之,人類學家與精神分析師都是在既有的知識與理論基礎上「參與觀察」,而且關切人的處境脈絡。過去,甚至有所謂的精神分析人類學這類的知識產出,通常是透過一種基於精神分析思想和理論的方法,特別關注影響人類生活和文化意義的無意識過程、情感和動機的性質。只不過到後來,這兩種學科卻存在著某種張力,甚至壁壘分明。英國的人類學家Kevin Birth(1994)研究了1917年至1935年間英國人類學教科書,他發現其實兩造之間是持續存在對話的,並沒有主要的概念對立;甚且,人類學甚至從精神分析中衍生出重要的概念。但到後來這兩門學科卻漸行漸遠,分道揚鑣,主要的原因或許是在於兩者都期待自己作為一種獨立學科,能夠更加的正統化。但這也不意味著兩個學科之間是如此格格不入,也依舊有人嘗試將兩者理論併用。
精神分析作為一種聆聽的類屬
不過,《聆聽的類屬》這樣一本書,在方法上更是別具一格。作者並不是將精神分析當作是一種理論,而是把使用精神分析的操作形式與使用它的人們當成是研究目標。這是一個橫跨語言人類學、社會文化與醫療人類學的著作,它將精神分析進行跨領域理論的解釋,並介紹它與阿根廷的近代史的關聯,最後說明精神分析如何充斥在阿根廷的文化生活之中,至為精彩。本書的一個重點在於將精神分析視為一種特定結構的語言類屬,而在阿根廷的社會脈絡中,「聆聽」則成為一種文化實踐的核心。
雖然這篇文章並不打算只有聚焦在書本介紹,但首先還是先交代一下這本書究竟說了什麼。本書的書寫一開始對「聆聽」這個身體化的實踐,進行跨領域的拆解分析,包括從語言學、符號學、音樂學等概念。透過這樣的介紹,作者更進一步的將精神分析定調為一種語言活動形式的「類屬」(genre);換言之,精神分析彷彿是一種特殊的語言,他建立在一種特殊的聆聽動機與技藝上,而作者觀察到,布宜諾艾利斯的居民似乎有意無意地特別能夠採取這種聆聽的方式。
作者從一個計程車上的對話開始,觀察到布宜諾艾利斯人的對話方式存在著某種「當你說X,我聽見Y」的互動公式,而全書就貫穿著這個概念。究竟,聆聽者為什麼有辦法聽見言說者的弦外之音呢?其實,如果熟悉精神分析的技術操作,便知分析師訓練的目標之一是能夠以一種聆聽的技術來察覺被治療者在治療空間裡的互動,即所謂的 “evenly-suspended attention”,或稱為”even hovering attention”。這意思是說,分析師(也就是聆聽者)並不會特定專注在話語中的任何特定部分,並允許無意識的自由進行;分析師則充分利用被分析者自由聯想的內容來思索對應規則,以分析其話語與行為的意義。換句話說,分析師關切的不是被分析者說了什麼,而是要彷彿將視角拉到一種俯瞰的高空,來探究為什麼被分析者要這樣說話。
那為什麼要把精神分析稱為一種聆聽的「類屬」呢?作者說,類屬本身創造了關係性的脈絡與框架,用以形塑聆聽者在接收訊息當下的方向。說白話一點,意思就是精神分析本身創造了一種聽取訊息的特殊語言機制,能夠用來了解一個人說話的脈絡與目的。作者在書中說明分析師聆聽的幾種方式,包括在聆聽過程中捕捉話語之中主客觀的意義,不但是一種同理的,同時也是互為主體的實踐。作者特別將符號學者查爾斯·S·皮爾斯(Charles S. Peirce)的類型學(typology)的概念應用在解釋精神分析聆聽方式,其實就是在這種特定的聆聽類型中,聆聽者的意向性被懸置。要訓練精神分析聆聽的能力,就在於能夠在這種語言形式中保持懸置狀態。此外,作者特別提及法國精神分析師拉岡(Jacques Lacan)的共振(resonance)的概念;在這個概念中,聲音在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之間迴盪著,且從來沒有完全實體化或固定下來,這樣的特性使的作者將這些互動理解為一種聆聽形式。
布宜諾艾利斯,一個聆聽者的城市
Dr Marsilli-Vargas在她的田野工作中發現,在布宜諾艾利斯,人們似乎有著像上述那樣能夠像分析師那樣聆聽並詮釋他們所接受到的話語的能力。於是,她進一步透過在分析現場的醫病互動,與日常生活的文化實踐的參照比較,並且爬梳精神分析理論如何進入阿根廷社會又透過學術機構發揚光大,並通過媒體傳播深入社會的過程,解釋布宜諾艾利斯如何成為成為一個「聆聽者的城市」。
當然,閱讀這本書時我所想到最困難的挑戰之一,應該是人類學研究如何尋找分析的田野。在這個民族誌中,作者介紹了一種很特殊的分析形式,也就是始於1960年的Multi-Family Structure Psychoanalytic Therapeutic (MFSTP)。這是由曾在巴黎受訓的醫師Dr. Jorge García Badaracco所發展出來的治療形式,本來是一種治療精神病與家庭關係的團體形式,在晚近被應用成為對於精神官能症(neurosis)的團體分析。本來非常隱密而一對一的治療關係,卻在阿根廷有了一種不一樣的實踐方式,也讓作者得以順利進入精神分析的田野。MFSTP的治療,有可能是幾十位案主家屬聚集在一個會議室裡一起進行,這涉及了一種分析逐漸公共化的過程。這樣的治療形式一方面可以說是與英國精神科醫師Maxwell Jones 所提出的,將治療關係民主化的「治療性社區」(therapeutic community)的理念不謀而合,同時也跟阿根廷的歷史與政治背景有很大的關係。
阿根廷的精神分析與拉岡有相當特殊的歷史關聯。作者提到過去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通過一種面向大眾的平民左翼運動進入阿根廷的左派;約莫在1960年代末,特別是拉岡的思想被引入,更加開明的左派才開始接受精神分析。此外作者也試圖解釋,布宜諾艾利斯人作為一個移民社會,它有著某種集體的憂鬱特質(melancholic character) ,而那所謂的失去母親的焦慮(motherless anxiety),使得人們更加急切地尋找精神分析能夠提供地某種共振(reassurance)的經驗,使得精神分析成為一種流行。由於這本書比較著重在語言學上的解釋,或許對布宜諾艾利斯人的社會處境的討論篇幅較為不足。作者在書中並不諱言地提到,精神分析如何外溢到治療的場域之外的這個現象,她較關切的是「如何」,而非「為何」如此。然而若要回答「為何」如此,或許可以由幾個我所聯想到的其他案例說起。
妮悉·達希爾維拉與巴西無意識意象博物館
如前所述,《聆聽的類屬》一書強調精神分析提供了某種聽的意識形態。這個意識形態似乎能成為阿根廷人在移民社會中與他人建立關係的基礎。我所想到的是,關於將治療的權力關係解放,或許也有一例值得記上一筆。如果布宜諾艾利斯人能透過特殊的聆聽技術來捕捉人們的意識與精神狀態,在1940-50年代的巴西也出現了另一種治療性實踐,那是由一位精神科醫師妮悉·達希爾維拉(Nise da Silveira)所發展的藝術治療。如果本書所提到的一種屬於聽覺的意識形態,則希爾維拉醫師的實踐就是一種視覺的;對希爾維拉來說,圖像即是一種來自於無意識的抽象語言。
以往熟悉精神醫療發展史的人都熟悉,過去精神疾病的治療經過許多的改革變遷,這當然與許多的因素相關聯,包括對精神疾病成因的理解,以及各種技術的發明。現在精神醫學的教科書都曾提及十八世紀的法國醫生菲利普·皮內爾(Philippe Pinel)將精神病人身上的鍊子給解開的「美談」。然而在抗精神病藥發明以前,精神疾病的治療仍使用監禁、電痙攣治療攣、胰島素休克治療或腦白質切除術。
或許是受到哲學家史賓諾莎(Baruch Spinoza)的影響,抑或她認同巴西共產主義的政治傾向,那種崇尚自由民主與挑戰威權的思維,也致使她在抗精神病藥尚未發展普及的年代,便開始反對那些對人體的侵犯性較高的治療。希爾維拉醫師則是觀察到在患有嚴重思覺失調症和慢性精神病症狀的患者,他們許多繪畫作品中出現了結構化的符號。當時,她也想要對非人道的治療提出另一種替代性的做法,因而發展了她獨特的藝術治療。希爾維拉本身也是受到另外一位重要的瑞士精神分析理論家榮格(Carl Jung)的影響。她從榮格那裡學到的理論與方法,促使她設立了「無意識意象博物館」,她研究精神病人圖畫中的符號並擴展它們的象徵含義,那些圖畫也在分析心理學理論架構中,能用以理解中那些未被揭示出來的身體症狀。「無意識圖像博物館」的藝術工作也影響了巴西的大學並且持續的發揚光大,並且持續影響著巴西的公共衛生政策。

圖二:Nise Magalhães da Silveira
有別於皮內爾所代表的歐洲中心精神醫學史,希爾維拉則給了一個屬於女性的、南方的實踐。這樣的治療形式,也與治療性社區的理念不謀而合。提出這個案例,也是企圖想要回應作者針對分析式聆聽所提出的,一種超越語言字面意義的理解方式,而這樣的方式本身是有治療效果的。而另一個想法則在於,精神分析理論在類似的脈絡下,成為一種擁抱現代性的方法,它所想要解決的,卻也是殖民下的權力關係。同樣地,希爾維拉作為巴伊亞醫學院期間唯一的女性,曾遠赴瑞士向榮格學習,最後來到里約熱內盧實踐她的理念;這一連串的個人實踐經驗也並非只是理論的移植,更重要的是她成就了一種具有性別與政治意識的,抵抗威權的範式。這些也使人進一步追問,為什麼無法被理解的症狀能夠透過特殊的聆聽或是觀看的方式被表達出來呢?精神分析在布宜諾艾利斯或是里約熱內盧是如何被擁抱的呢?這究竟是否跟殖民的歷史是否有些關係?
被殖民者的語言與聆聽的動機
作為一本語言人類學的著作,作者是將精神分析當成一種特殊的語言,換句話說,精神分析的操作形式本身就自成一種語言邏輯。但閱讀此書,作為一名生活在多元族群社會中的讀者,依然會對一個後殖民社會中的語言使用有些好奇。精神分析在阿根廷盛行、流傳,固然是以西班牙語為主。然而即使是使用西班牙語,是否也有些屬於阿根廷社會不一樣的語言使用方式呢?我的問題來自於我對西班牙的歷史與族群、語言使用的好奇,由於西班牙過去也是殖民社會,也有原住民語言。那西班牙語在阿根廷的使用是否有其特殊之處?如果問的更詳細一點,我想知道布宜諾艾利斯人的人群組成是什麼樣子呢?而克里奧白人的語言又與歐洲的西班牙語有什麼不一樣?阿根廷的原住民的處境又是什麼?由於受到殖民的影響,語言有時候在文法、字彙與時態上都可能有些不同,甚至在布宜諾艾利斯,有種高度受到移民語言影響的Lunfardo, 這在同樣盛行在布宜諾艾利斯的探戈(tango)音樂歌詞中相當常見,而這是不是也會影響了阿根廷的精神分析的語言呢?
這些問題,源自於我對台灣原住民的觀察。現在台灣使用中文的方式,在原住民、福佬客家人,以及在中國內戰後移民至台灣的外省人,對中文的掌握跟使用是相當不一樣的。原住民在使用中文上有更特別之處,包括他們更容易使用諧音,文法上使用倒裝句,或是開中文的玩笑,或許也有一種你說X但我故意說Y的意圖。這種語言的意識型態,似乎存在者某種對殖民語言的刻意扭曲與抵抗,一部分可能來自於自身被壓迫與邊緣化,以及語言的剝奪。
此外,作者在書中也曾提到在偏遠地區或在一些有少數原住民社群中,那些移民官員也發展出某種「聆聽謊言」狀態,這很有可能是源於某種文化距離。換句話說,那些移民官員因為文化的隔閡使得他們對少數族群的話語產生某種程度的不信任。那麼令人好奇的正是,作為一個後殖民社會,這種存在於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距離,是否可能成為一種更需要聆聽的動機呢?(註三)
治療作為一種流行,幾個比較案例
本書的第四章有提到,阿根廷有個有趣的說法:「在布宜諾艾利斯很缺工程師,但卻有一拖拉庫的精神分析師。(In Buenos Aires there is a lack of engineers and a surplus of psychoanalysts.) 這與我目前所執業在的城市——新竹,正好恰恰相反。在新竹有一拖拉庫的工程師,卻幾乎沒什麼分析治療師。在台灣經濟發展政策下,新竹成為一個高科技電子工業集中的城市,但這些工程師處在高壓的工作環境中,鮮少會借助心理治療,反而高度仰賴助眠藥物與抗焦慮藥物、抗憂鬱藥物,來使自己維持在一定的工作效能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在於,竹科工業的勞動條件非常嚴苛,整個竹科也無法組織與體制對抗的工會,因此幾乎很難改變勞動條件。再者,台灣有很便宜的健保系統,使得人們可以簡便的透過藥物來維持功能。
我對這個現象的理解在於,人們的健康尋求行為(health seeking behavior)一方面取決於人們對受苦經驗的理解,也取決於外在的政治經濟的條件。一旦人們將自己的受苦經驗命名,也形成了某種自我認同,這也成為一種詮釋自己的狀態的基礎。換言之,「醫療化」反而成為竹科員工逃離體制的一種出口。這和過去社會學家所指出,要不是醫療權力的擴張,就有可能是受藥物工業推波助瀾的那種醫療化現象(Lakoff 2006; Conrad 2007),是不太一樣的。事實上,當代社會中某種特殊治療的流行,是許多因素交織而成的,而這我所想到的有兩個相當有代表性的案例,分別是中國的心理熱與日本的榮格分析。
台灣陽明交通大學的醫療人類學家黃宣穎老師曾在中國進行心理治療熱潮的研究,他在研究中提到了心理學在現代中國不同時期的政府政策和民間社會中的接受歷史(Huang 2015)。近年來,尤其是在2000年之後,這股「心理熱」在中國的城市地區出現了一股趨勢,這與《聆聽的類型》中描述的情況有些相似,心理學通過大學和大眾媒體在普羅大眾中獲得了流行,這種現象與中國的政治和經濟變化有關。黃宣穎指出,「心理熱具有雙重性格——它既是經濟進步的產物,也是對進步帶來的問題的治療手段。」然而,我認為我們應該意識到,在中國和阿根廷,參與心理治療或心理分析的參與者可能不屬於同一類別。一些人可能會從專業化的過程中受益,而其他人可能迫切需要解決他們的心理健康問題。
另一個案例則是日本人類學家北中淳子曾經為文說明榮格學派心理治療在日本發展的過程(Kitanaka 2003)。事實上,在195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日本社會普遍存在著某種渴望民主的集體氛圍。人們渴望自我實現,但又不想透過直接的支持,這使得心理學在日本社會中有了成長的基礎。而美軍在之後佔領日本並且廣設各種心理學相關的機構,包括兒童矯正機構或是精神病院;加上1970年代的反精神醫學運動,提供了精神分析發展的空間。然而讓榮格學派在日本有更多發展的關鍵人,不外乎是河合隼雄。他不僅將榮格的作品引介至日本,並且致力於將日本的社會文化的特性與榮格的心理學做一種結合。
河合隼雄不僅將榮格的作品引介至日本,並且發現日本的社會文化的特性是榮格心理學在該地發展的根基。比方說,從日本的民間故事或佛教精神,可以發現與榮格心理學的共通之處。榮格的理論給了日本文化批評的養分,例如榮格所謂偉大母親的概念,也讓心理學家用以解釋日本普遍面臨父親缺席的日本社會。北中淳子提到,正是這些心理治療師能夠表達出未被命名的焦慮,促使心理治療成為媒體中受歡迎的自我反思和社會批判工具的能力。但是無論是拉岡在阿根廷,榮格在日本,或是中國的心理熱,這些當代流行起來的治療,更意味著民俗醫療本身不只是文化的,更是社會與政治經濟相互糾纏的產物。
精神分析是一種解殖的實踐嗎?
有意思的,是精神分析作為一種文化實踐,它本身是一種外來的理論,某種程度來說,或許有種在知識上的殖民的狀態,也就像是書中也有提到的霸權姿態(hegemonic presence)或文化威權(cultural authority)的概念。但是在阿根廷,精神分析並不只是被知識菁英壟斷,反而是被大眾所接受的。那麼是否可以說,擁抱精神分析,也能視為是一種以一種創新的文化實踐,而做為某種抵抗呢?如果是的話,它是用來抵抗什麼?因此我想提出的問題是,精神分析是否是一種去殖民的實踐工具?
作者一度將精神分析的盛行比擬探戈的流行,認為阿根廷人渴望被擁抱。多年前,政治理論與人類學者Marta Savigliano(1995)便著述Tango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assion一書(暫翻《探戈與激情的政治經濟學》),她在書中反覆提到解殖/去殖民(decolonization)的概念。簡言之,去殖民成為她詮釋探戈的流行的核心論述。也許讀者會對此時提出去殖民有所困惑,畢竟阿根廷已經獨立了接近兩百年了。但是Savigliano這樣說:「去殖民化是一個不斷進行的目的,一個尋求自決的探索,一個解放的過程。去殖民化是無窮盡的。此外,去殖民化不是一個終點的問題,而是一個關於忠誠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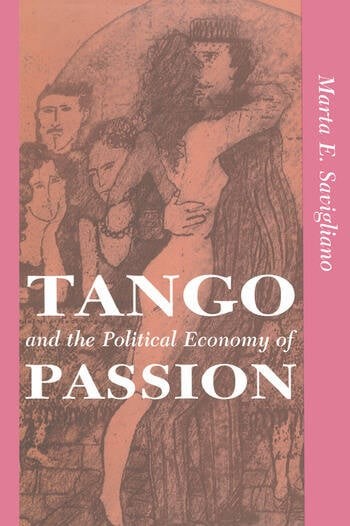
圖三:Tango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assion封面
精神分析盛行的這一世紀以來,阿根廷社會仍存在現代化與民主化過程的諸多矛盾與政治暴力。更進一步說,是否可以說,精神分析的盛行,是否也能象徵著在後殖民社會中的某種自我解殖的實踐?也就是人民必需通過一種超越殖民語言的形式,在互為主體的聆聽過程中,重新建構出一種新的主體性。如果說,精神分析是一種人民渴望他們的社會性受苦被聆聽的解方,雖然這個社會現況似乎在本書的著墨並不是很多,卻也可能能作為這本書對於「為何」精神分析會成為流行的一個補充。換言之,精神分析或可成為一種以新的文化實踐(一種新的身體化的語言形式)用以抵抗他自己持續所經歷的社會受苦的方式,又或者是用以抵抗他們在後殖民情境所經歷的各種社會矛盾的方式。
最後要說的是,這本書的書寫方式非常有創意也具有啟發性,然而因為較聚焦於語言的分析,某種程度似乎犧牲了一些篇幅來記錄人民的生活樣貌,這是較為可惜之處。另外,許多推廣精神分析的行動者本身一定有更豐富的生命故事值得了解,例如創立阿根廷精神分析學會(Argentina Psychoanalysis Association)的Marie Langer,她後來因為政治因素必須流亡至墨西哥城,這些過程都讓人產生更旺盛的好奇心想知道更多的細節。但我想我必須先停在這裡。但我還是要再次謝謝Dr Marsilli-Vargas為我們帶來如此精彩的作品。
後記:
作為精神分析的學習者與使用者,同時亦身為人類學的學徒,能有機會與這樣一本特殊的民族誌作者進行對談,自是感到相當榮幸。這篇書寫或許發散,也算是一種「自由聯想」一般的回應。不得不說,這些內容也有許多也是個人關懷的投射,有些提出的問題,也尚未有具體的答案。撰寫此文的當下,我反覆憶起當年從英國東北小城通車前往治療的路途上,途中經過的北方天使雕像,以及巴士的汽油味,乃至於治療室外面的等候區播放的安魂曲;這一切都成為生命中特殊的符碼,成為恐慌發作時能夠安頓自己的記憶。願每個人都能找到屬於他自己的樹洞、石洞,以及治療室。

圖四:作者前往治療室的途中所攝
註解
註一:這篇文章源於2023年6月8日,由政大民族學系主辦的《精神分析與民族誌研究》專書討會,感謝劉子愷老師的邀請與主持。
註二:本對談稿是以當天的對談回應再加以增補改寫而成。
註三:在此處,作者的回應是,在布宜諾艾利斯,那種族群的語言使用與族群的組成,相對於在墨西哥,反而是比較單一的。
參考資料
Birth, Kevin. 1994. “British Anthropology and Psychoanalysis before World War II: the Evolution of Asserted Irrelevance”. Canberra Anthropology 17(1): 53-69.
Conrad, P. (2007). The Medicalization of Society: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Human Conditions into Treatable Disorder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Huang, Hsuan-Ying, Psychotherapy to Psycho-Boom: A Historical Overview of Psychotherapy in China,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therapy in China , Volume 1, 2015: pp. 1–30.
Kitanaka J. Jungians and the rise of psychotherapy in Japan: a brief historical note. Transcult Psychiatry. 2003 Jun;40(2):239-47.
Lakoff, A. (2006). Pharmaceutical Reason: Knowledge and Value in Global Psychiat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Marta Savigliano (1995) , Tango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assion. Routledge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吳易澄 當一座城市成為治療室——《聆聽的類屬》的自由聯想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index.php/article/7002 )



回應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吳醫師這篇有很多的聯想,觸及我內在也曾經有過的聯想,比較阿根廷跟新竹的政治經濟局勢形塑出的人類樣貌,以及阿根廷的精神分析、中國的心理熱與日本的榮格分析,與殖民與去殖民化的過程闡述,都讓我讀完之後印象相當深刻,感謝吳醫師的分享。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