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吉拉‧921‧一個紀念不了的紀念
我知道2019年6月3日此時寫芭樂文,很難不被安排要寫點有關六四即將滿三十周年的議題,特別是我這幾年研究香港;或是可以寫點有關即將到來(有嗎?有吧?)的台灣二大黨總統初選,特別是我去年寫了篇題名「疲倦民主」的芭樂文。前者事件充滿了「我們不能遺忘歷史」的呼喊,後者事件呼喊著「我們要書寫歷史」。無論如何,上述二件現在進行式都召喚著眾多人們變成「我們」,做歷史的主體,在線上與線下。然而,我卻被正在台灣院線上映的《哥吉拉II怪獸之王》所吸引。我不是一個真正的哥吉拉(Godzilla)影迷,我也不是一個怪獸迷。我之所以注意到哥吉拉,是在寫博士論文要處理災難研究的文獻時,接觸到著名評論家 Susan Sontag寫的一篇小文章“The imagination of disaster” (收在她的評論集 Against Interpretation,1966),裡面提到日本導演Ishirō Honda的科幻電影,而他的代表作即是1950年代出品的《哥吉拉》。Sontag說:「科幻電影不關乎科學,其實是關於災難。」(p.213)哥吉拉的名稱經過幾次變化,它的形象也經歷了多次變化,最早的哥吉拉是一部受到金剛影響的怪獸電影,描述受到核子幅射污染的海域中出現一隻身高達50公尺、狀如恐龍的怪獸「哥吉拉」,從幽深的海底如復仇者般毀滅大半個日本。到了好萊塢接手續拍系列電影之後,哥吉拉從攻擊人類的怪獸,化身為可以和人類共存的生物,一起努力重復遭到人類破壞的大自然平衡(簡要的演化歷史請參見中文維基哥吉拉條目)。是的,哥吉拉一直在演化,伴隨著人們(現在已跨出日本)的不安而演化,它在大眾文化裡自成文類,似乎有了自己的生命,它可以是個隱喻,是個寓言,從人們如海底一般的潛意識裡投射出來。如同人類學探討怪獸的文獻所指出,怪獸的英文monster字源有二層意涵,一是警告,一是顯現。怪獸顯現出人們分類的模糊性,湊合了熟悉和陌生的事物,既安全又遙遠,飽含預言和警告的神奇之物(Yasmine Musharbash,Monster Anthropology in Australasia and Beyond,2014,p.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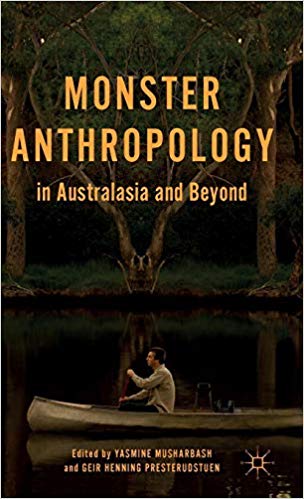
無論哥吉拉的起源和形象如何變化,其出身倒始終不變:它乃深睡海底千年的史前巨獸,偶然被人類的核子試爆給喚起。因此,日本版的哥吉拉明顯受到日本曾經遭到原子彈轟炸,以及1950年代冷戰時期核子大戰所影響;相對的,好萊塢版本的哥吉拉反而將核子能源變成它的戰鬥力來源,來對抗威脅地球的其他巨獸。Sontag所說的「對災難的想像」卻也是對集體創傷的出口,而科幻電影更像個出口,試圖將這個魔怪所象徵的創傷給驅魔掉(exorcize)(p.218)。那是多大的集體創傷造成如此巨大的怪獸?我想。歷經多年,形態多變,穩固佔據著(日本)人們集體想像的一角。而且如上所說,哥吉拉已成了大眾文化工業的一環,某種程度被「洗白」了,加入當代恐龍、怪獸迷文化,具有神奇力量,甚至可以和人類溝通。
哥吉拉從海底深處竄出,每隔一段時間;而每隔一個五年、十年,有關921大地震(1999年)的種種也會從台灣人的記憶裡竄出。是的,今年(2019)將是921大地震20周年。朋友問我這個曾因博士論文田野調查而遭遇到921大地震的人,甚麼是台灣921大地震的哥吉拉?為何台灣921大地震的「集體創傷」沒有產生哥吉拉?這個「集體創傷」找到甚麼樣的出口呢?如果即將滿三十周年的六四事件仍然影響著當事人以及有關、無關的人,那921大地震屆滿20周年後,還在影響當事人以及甚麼樣的人呢?如何影響?如果歷史沒有忘掉我們,我們沒有忘掉歷史,1999年此時也正是台灣政壇暗潮洶湧的時刻,二大黨群雄佈局角力即將到來的千禧年總統大選,最後竟「也是」三組總統候選人。然後,就在秋天,發生了921大地震。那時人們說,因為災難,因為重建問題,重創了當時執政者國民黨的信度,造成了台灣第一次的政黨輪替。大地震讓中部幾個重災區幾乎夷為平地,人們站在焦土上急著恢復舊貌,掩埋創傷,讓挖土機重建思維主導。如果當年可能有一點不同,20年之後此時的總統大選會不會不是發展再發展的純經濟思維主導大選主軸?人們說,我們應該從災難中學到教訓,所以我們錯過了甚麼嗎?朋友和我一連串的對話,我沒有答案。答案或許在哥吉拉,或許沒有,於是我買票進場看哥吉拉,嗯,聲光效果不錯。為免有宣傳該片的利益衝突之嫌,這個形容就可以了。

當然,我不是只有進場看哥吉拉,我也嘗試想做點事情,紀念這個事件。於是我抽空從台北到中部「災區」看看(其實不能再用「災區」這個字眼,以下只是為了行文方便而用,請讀者諒察),拜訪朋友,雖然我從來沒有離開。但是,我的新一波「危險」就此開始(請參看《田野的技藝》一書,的確有宣傳該書的利益衝突之實)。首先,我是誰?我不再是當年剛好身處其中的研究者,我不是災民;我不是已經離開了嗎?若單純是個人知識興趣的延續,我應該不是歷史記憶要召喚的主體。反倒是仍在中部地區的團體和政府單位,有著明確的主體位置與某種程度的道德義務。據我所知,在地已經規劃不少的紀念活動,有些是在既有的年度活動安上921大地震20周年紀念之名,有些則是十年周期的專門活動(同樣也有為活動宣傳之嫌)。大家可以注意,夏天過後,類似活動將陸續展開,預告將會到臨的回顧與創新,官方版本的。最難也最具危險性的面向則是,為什麼要紀念?我要紀念甚麼?朋友說,對災區之外的人而言,921地震在災難發生幾個月之後就結束了;也有人說,20年了,即使連災區的人也早已告別傷痛在過平常日子。又有人說,明年可以選總統的首投族泰半對921地震並沒有切身感,他們不是遺忘,而是根本沒可能記住,因為平地早起高樓,焦土變成黃金。另外的人質問我,好,我們一起來做吧,但要說甚麼呢?20年了,還有甚麼該說的還沒說呢?況且,不是有不少人們還在持續說著嗎?比方說,十幾年來,政府和社區不斷要「讓災區站起來」,一個接一個的計畫,農村再生、培根社區、軔性社區、文化復振、一直到晚近配合其他社會狀況變化推出的社區長照2.0、地方創生等等。當然以上這些計畫不限於災區,只是在災區推動時,總會在計畫前言以起源故事般向921地震致意。也就是說,災區似乎也沒忘了921地震,不停在訴說它。

所以,我(們)要紀念甚麼呢?我們錯過了甚麼嗎?災區的人無論如何都未必會停一下想一想20年來個人和周遭社會的變化,我們要如何打動災區以外的人,讓人們有感呢?
以上的他人詢問和自我質問都是非常基本而重要的,我也理解如此龐大的事件,牽涉如此多的人以及社會力量,加上漫長的20年歲月,實非一場單一的紀念活動可以承載。每個人看待這個事件的視角、與這個事件的關連程度都不同,即使同一個人,20年下來必也經歷了極大的改變。彷彿一潭寬廣但清澈的湖水,很容易就可以望進湖底,但是我們只是隔著水體看著湖底的沙土水草,沙土水草之下又有甚麼呢?湖到底有多深?我們想看清楚,卻擾動了一潭清澈,沙土泥濘混亂,反倒使得湖水渾濁,再也不容易看清了。或許我們不要再攪動它,免得驚動深藏湖底不知何在的千年史前巨獸?幽靜清澈的湖水啊,當我們不去干擾的時候。想紀念921的初衷清楚直接,我認為一個社會若是沒有記憶或失去記憶的能力必然危險,所以千萬不要問香港人為何要紀念六四,即使三十年之後。同樣類似地,一個社會如何關連它的創傷恰恰顯示它如何了解自己、它的世界觀,以及它要扮演的角色。於是921地震之後,台灣沒有哥吉拉,或許不是集體創傷的程度不如遭受核爆的日本,也可能不是台灣文化不擅長以魔怪來象徵化集體創傷,我想也許是我們想把它深藏海底。921地震在我學術生涯初期起了極為重大的影響,除了知識上想要了解災難的意義之外,情感和存在的層面上,我也必須找個出口。因緣際會之下,我當年接觸到時間和空間尺度都距我不遠的村上春樹短篇小說集《神的孩子在跳舞》(2000),其中多個故事以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為故事的背景,而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是台灣在幾年之後921地震常常借鑒的事件。村上春樹接受訪問曾說,1995年可說是他人生與寫作的轉捩點,從一個創作小說家兼及紀實文學的視角,持續記錄影響日本社會的重大事件發生後的種種狀況,包括記錄沙林毒氣攻擊的《地下鐵事件》。於是,我斷續但持續地記錄著921地震之後種種。我理解也嘗試提升個人層面的關懷,期待能夠連接到更大更廣的層面,村上春樹的方法是小說,讓作品可以打動更多的人;我的921地震研究論文大概只能限於學術界。那麼,辦一場紀念活動如何呢?只是這個攪動湖水的舉動,讓我觸及密密麻麻縱橫交錯的沙土水草,我雖然有所準備,但仍然超乎我的預期。我越想看清湖的底限,卻越來越覺得我自己原來也是沙土水草的一部分,我從來不是外來的探湖者。終究,這是一潭難以澄清的湖水,難以說明白的回返紀念。或許我應該需要一個哥吉拉。
我寫921大地震20周年的紀念文章大概是必然,但是寫成這樣子的紀念文章卻是偶然,全因紀念不了紀念的緣故。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容邵武 哥吉拉‧921‧一個紀念不了的紀念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index.php/article/6722 )



回應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日文(語)的大猩猩+鯨魚=哥吉拉,當時創造哥吉拉背景是希望有社會反思性質的,1954初代哥吉拉象徵日人對戰爭與核能的恐懼,之後轉化為怪獸對決,轉向正義角色,影片脈絡從災難性轉變科幻,再走向兒童性質,挾帶著票房下滑,1975停拍,(以上為昭和系列); 之後換成平成系列哥吉拉,又是一個重新的開始,....2000千禧哥吉拉,有獲得了美國MTV頒發的終身成就獎,接近一位實質明星的存在, 所以對於一個災難事件,從哥吉拉的起源來說從實質災難需構一位怪獸,中間起起落落,到最後變成全人類的實質明星,並轉化為正義的代表,把災難的記憶化為有形(好萊屋星光大道星形獎章)與無形深刻心中記憶(隨時代科技演化蛻變與重覆), 對於災難,我也認同我們需要一個 哥吉拉 , 老師好 好久不見歐!!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