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的根源與路徑
小編前言
詹姆士・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的「人類學反思三部曲」:《文化的困境:20世紀民族誌、文學與藝術》(1988)、《路徑:20世紀晚期的旅行與翻譯》(1997)、《復返:21世紀成為原住民》(2013),蒙科技部(現在的國科會)經典譯註計畫以及東華大學林徐達教授的不懈努力,已經陸續翻譯出版。桂冠出版社於2017出版《復返》,2019年出版《路徑》。然而,隨著桂冠出版社創辦人的不幸離世(2019)以及出版社結束營業(2022),讀友們已經很難再買到三部曲的中譯本。謝謝左岸出版社接力完成這項重要的出版計畫,去年底推出《文化的困境》,今年重新出版《路徑》,讓中文世界的讀者們得以接觸到這套值得一再重讀的人類學反思經典著作。
專長藝術人類學與表演人類學的謝一誼老師,近來就在重讀《路徑》的過程中,發現了身兼人類學者、部落工作者、被部落族人賦予要求與責任的部落孩子等等複雜旅行路線的吳明季老師,在2019《路徑》中文版導言中,已經觸及當代台灣原住民藝術所探討的重要議題。這篇導言已經絕版,因此謝一誼老師特別徵得原作者的同意,在芭樂人類學重新刊出,邀請對當代原住民藝術有興趣的朋友重新閱讀這篇文章。你一定能夠透過此書中的路徑思考,得到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從藝術人類學看「路徑」
研究自己家附近的事,訪問自己的鄰居,這是人類學嗎?新型態的「拼布民族誌 (patchwork ethnography)」方法論,近來開始積極反思「家vs.公共」、「我群vs.他群」、「研究者的家vs. 遙遠田野」這些人類學的經典範疇 (Günel & Watanabe 2023 )。屏東大學的吳明季老師,長期在奇美部落與族人共同努力、創造團結經濟,在這篇2019年「路徑」繁中翻譯第一版(桂冠出版社)的導言中,超前部署地站在台灣的角度,回應「拼布民族誌」這幾年才提出的有機民族誌方法論。這篇導讀不僅幫助我們具體的想像一種實踐先行的、合作型的、落地又深具世界主義的原住民研究,可以是什麼樣貌; 此篇導讀還闡述了怎麼和鄰居一起做人類學,以奇美部落的經驗,提出當代原住民有機的跨國跨洋聯盟,更回應了James Clifford 在《路徑(Routes)》(1999)與《復返(Returns)》(2013) 兩書中提出的諸多問題。
2024年,「路徑」一書繁中二版誕生(左岸出版社),讓我們一起隨著吳明季老師在2019年為第一版翻譯所寫的導讀,回顧這些在20世紀末被提出的重要問題。我們可以用複雜、有機的「路徑(routes)」,取代「根源(roots)」,作為人類學的研究軸線嗎?研究者自己的族群、階級、性別定位,怎麼納進當代人類學在面對種種交會時,所蹦出的火花?James Clifford怎麼面對「挪用」、「觀看」、「展示」這些原住民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的重要問題?炎炎夏日,關心藝術人類學與表演人類學的朋友,不要錯過這篇精彩導讀,更不要錯過2024年「路徑」新版的更多討論!
謝ㄧ誼 (陽明交大人社系與族文所)
同場加映:
「失譯招領」(Lost and Found in Translation):《復返》出版序(林徐達)
《文化的困境》導讀:馬林諾斯基遺產與當代民族誌覺察(林徐達)
《文化的困境:二十世紀的民族誌、文學與藝術》(「如是文化,如是族群」對談之夜記錄)(李宜澤)
《路徑:20世紀晚期的旅行與翻譯》
導論:原住民的根源與路徑(吳明季)
二戰後,全球各地的殖民地捲起一波獨立運動的浪潮,並在接下來幾十年內,勢不可擋的一波又一波成為形式上獨立的國家。去殖 民化的反思風起雲湧,過往人類學與殖民主義過從甚密的關係,無所遁逃的被一一挑出、批判與指責。面臨人類學正當性的危機,以及整 個田野環境劇烈的轉變,在這樣的氛圍下,二十世紀最後的二、三十年間,許多人類學家紛紛對於什麼是人類學?什麼是田野工作?提出 相當深刻的反思,人類學這門學科也在這樣的反思下逐漸轉變。詹姆斯・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的《路徑》一書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於一九九七年出版。
人類學是一門透過跨界取得知識的學科,田野工作是取得人類學知識最主要的方法。二十世紀初馬凌諾斯基(Malinowski)及其學生們建立民族誌田野研究方法與規範後,「搖椅人類學家」已被視為不具正當性。每個人類學初學者都要動身前往遙遠的異地,在某個劃定出來的範圍內,住上一年以上,學習當地的語言,在田野嚴苛與不確 定性的環境下,認真的參與觀察,研究當地他者的文化。
到了二十世紀後半期,人類學家逐漸發現進入田野不再像以前 那麼方便,正如葛茲(Geertz 1995)所指出,進入田野不再有以往的(殖民)特權位置,在田野中與其他共同工作的人的相對位置改變 了,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關係更敏感、更難操作。與其他研究領域的關係、人類學的興趣清單都已經非常不同。現在,田野工作幾乎不可 能在沒有其他學者在場(或至少在附近)的地方進行,在知識界,民 族誌學者曾是他們所調查對象的知識權威,只因為他們是唯一抵達這 些地方、研究這些事物的人。但現在,民族誌學者的工作受到許多不 同類型專家的批判眼光所檢視,有時也跟這些專家合作。甚至,現在 許多當地人加入了人類學家的行列,民族誌田野也必須接受人類學內 部更具洞察力的批判眼光。
田野的環境已經大幅改變,正如克里弗德在《路徑》書中一開頭 就引的例子,印度裔學者高緒(Amitave Ghosh)在埃及做田野,現在,埃及已經不是所謂「古老並安居」的田野地,而是世界各地旅行者來來去去的地方,高緒也不再是純粹「西方」的學者研究「東方」的原住民,在這個人類學田野中,有各種複雜的、流動的、支離破碎的關係,世界已經改變,人類學家要如何理解「田野」?理解「接觸」?理解當今「離散」的世界?克里弗德說,讓我們試著透過「旅行」的概念來理解與鬆脫過往人類學對田野及知識僵固的想像。因為當代人類學的田野工作,或許是每天搭著地鐵到離家幾哩遠的地方去「深度閒晃」;或許是到遙遠的他方,但該處的人們早已透過飛機、 電話、網路而全世界來來去去穿梭自如;或許網路社群的新聞群組討論就是某個人類學家的田野;也或許有些原住民人類學者的田野就是 自己的「家」。半個世紀以來,去殖民化的批判與抵抗、科技進展造 成的時空壓縮、大量離散人口的出現、現代國家與資本主義的全球滲 透等等因素,當代人類學田野已經沒有與世隔絕的原始部落,田野工 作的方法與概念也不再有條件與馬凌諾斯基那個年代相同。
克里弗德(2013)認為,一九八八年他出版《文化的困境》一書,關注的是西方的去中心化,權力關係與論述位置(discursive location)在戰後去殖民化的過程中已深深轉換,儘管西方霸權至今仍然以各種方式存在。一九九七年出版《路徑》,關注的是對位置(location)和流動性的複雜意識,去中心化與眾聲喧嘩不僅是去殖民化與全球化的結果,也是一種新形式資本主義的產物,如何跨界?如 何接觸?需要對各種交互傾軋的流動力量更敏銳,也更有面對和分析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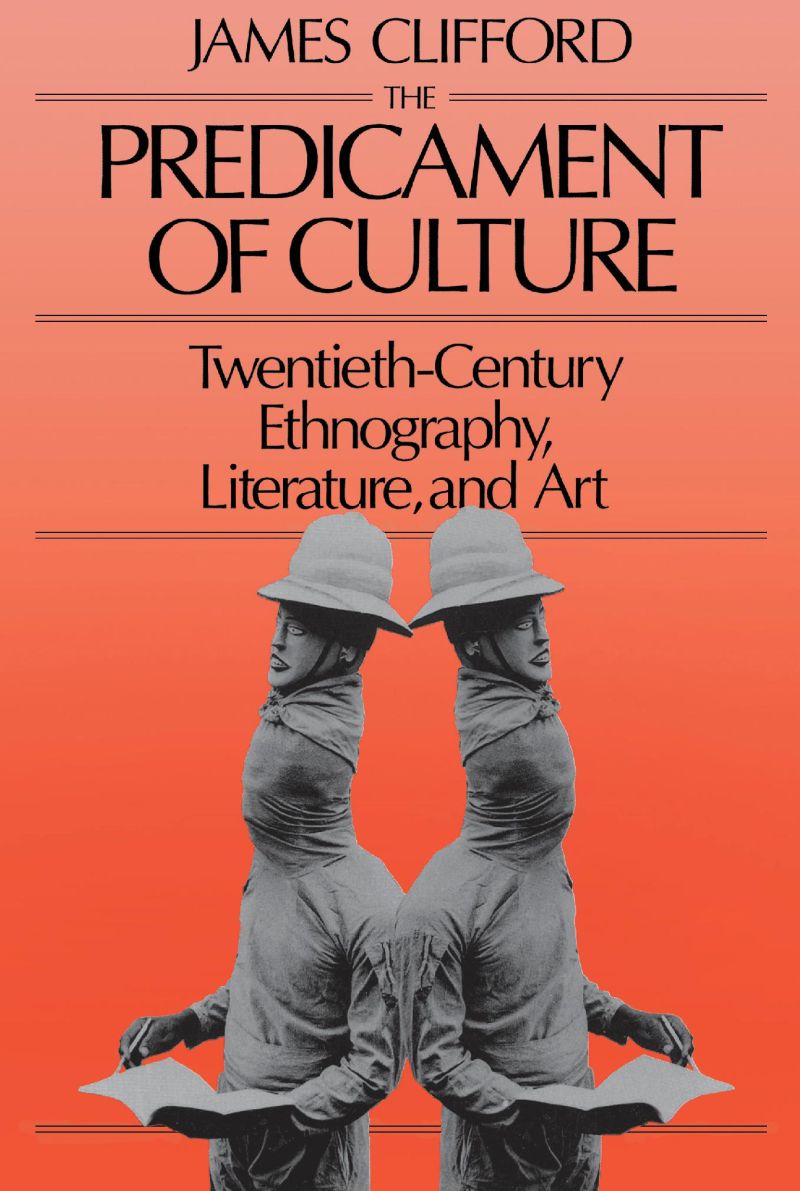
Clifford, James.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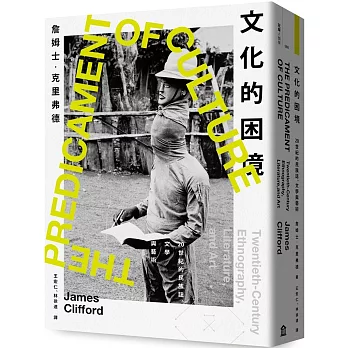
詹姆士.克里弗德,《文化的困境:20世紀的民族誌、文學與藝術》。王宏仁、林徐達譯。左岸出版。2023。
在這個年代,人類學進入田野的遊戲規則早已經改變,田野變了,人類學也改變了。過去人類學的知識生產,是建立在假設這個世 界存在許多不同的、獨特的「文化」,以及「我們的」社會與「他們的」社會之間毫無疑問存在差別。一種對立的形式被接受:「這裡」 和「那裡」、「我們」和「他們」、「我們的社會」和「他們的社會」。使得人類學家知識生產是建立在這樣的假設之上:這個世界上有和我們不同文化的他者,在遙遠被隔離的地方、被隔離的歷史,等 著人類學家去發現,他們的文化差異是他們社會歷史過程的產物,與我們的社會歷史是隔離的、不連續的。人類學家到「他們」「那裡」的交遇,建構出「我們」「這裡」的批判(Appadurai 1988;Gupta & Ferguson 1997)。
這樣研究異文化他者的設定,是有權力階級的,並且也囚禁、限制了在地人(natives)的能動性(Appadurai 1988)。在地人就是待在那裡不動的,而探險家、殖民官員、傳教士跟人類學家是可移動的、會去到那個地方、看到和知道的人(意思是前者不是喔)。當觀察者來到時,在地人也不是不能動,只是他們的移動被視為敗走、逃離到另一個被限制的地方。更細微的看,這樣的概念下發展出來的 知識也是有階級的:田野地的在地知識、語言和技術,都是一種受囚禁、有限制的語言與知識。就算在地人(natives)移動的距離很大,但跟西方都會型態那種自由、任意、探險的行為是不一樣的移動在 這種知識概念下,土著性(nativeness)是一種被拘留的概念,並且土 著是被自己的所知所感所限制,被自身思維模式所監禁,這些概念隱 含著道德與智識的判定。所以,阿帕度萊(Appadurai)不客氣的指出,我們會稱生長於紐約的在地人為土著(natives)嗎?
費邊(Fabian 1983)考察時間性與人類學他者的關係,發現「共時性的否認」是過往人類學的主要潮流。人類學家透過田野工作 與他者溝通互動,這部分的研究是共時性的,但是研究與書寫上出現 重大的矛盾,因為人類學的書寫卻是採取異時性的論述。人類學家筆下的「土著」彷彿居住在某個古老年代,而不是與人類學家同時代, 這種時間概念是透過書寫編排出來的,並且強加於民族誌「他者」的身上。當人類學的異時性概念不斷被鞏固,在此概念下的他者也被符 號化,內化於論述中,表現在象徵關係中,他者成為符號學的他者, 並在人類學知識生產的過程中被客體化。這種客體化需要仰賴距離、 空間、時間來形成,這意味著客體必須與研究者保持一個清楚可分的 距離。所以,他者性、野蠻與原始並沒有被西方「發現」,而是被部 署。民族誌書寫透過操弄「暫時性的共存」及「共時性的否認」來極 力維持研究者與「他者」的距離。
當代人類學面臨的不僅是田野地點選擇的改變,連帶的,包括田野的定義、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位置與關係、以及隱藏在田野工作與 人類學知識生產背後的許多假設與權力關係都已經被挑戰。古塔和弗 格森(Gupta & Ferguson 1997)認為必須從空間與文化差異關係的概念提出根本的質問:如何解釋在地的文化差異?後殖民揉雜的文化屬於什麼?殖民遭遇創造了一個「新的文化」嗎?相臨的獨立國家卻有 不同的社會變遷與文化改革,又該如何理解?靈活積累的機制取代了福特主義模式,小批量生產、生產線快速轉移、資本快速移動,建造 了一個複雜的溝通和信息網絡,以及更好的轉移商品和人群的方式;同時,工業生產的文化、娛樂以及休閒的全球經銷,這些都破壞了斷裂、隔離的空間想像,創造了新形式的文化差異與想像共同體。在這 樣的田野中,該如何面對與理解?並找出自己與研究對象的關係性位 置與論述位置?
克里弗德(1997)認為,人類學家就是一個旅行者,但是他們跟 一般喜歡旅遊各地的旅行者不同,他們會在海外找一個定點,久居一 段時間深耕他們的田野。正如葛茲(1995)所說的,人類學家不是研 究部落,而是在部落「中」研究。雖然現在人類學家的田野越來越多 並非在「原始的」部落裡,甚至就是在都市、醫院、觀光飯店、科學 實驗室……進行研究。但克里弗德指出,儘管離開了真正的部落,田 野工作作為一種獨特在地化「定居」的概念依舊存在,並且是偏重定 居的關係,而非旅行的關係。克里弗德提醒,要對這樣的田野規範實 務保持警覺,因為這是將研究對象在地化與客體化的策略,並內化於 人類學知識生產當中。民族誌論述「在哪裡(being there)」和旅行「到哪裡(getting there)」的概念完全不同,且民族誌的論述、書寫大量抹去人類學家旅行成分諸如交通工具、旅行前的聯繫、翻譯的關係、以及與當地原住民的參與合作,塑造了「當地人說話,人類學家 書寫」的人類學家霸權關係。克里弗德希望藉由將天平的法碼推往旅行的那一端,但並非單純的將「旅行」取代「定居」,也不是天真的 民主式多重作者,而是要關注社會文化的多重外部連結,思索如何再現在地與全球的歷史相遇、合作、支配與鬥爭的群相,認真看待混雜 的概念,以及世界主義的經驗。如同過往民族誌重視在地的、當地人一樣重要,要用這種意識來突破再現的本質化。
在《路徑》一書中,克里弗德舉了許多例子說明,最極端的例子是夏威夷的 Moe 家族,他們是一群音樂家,在二十世紀的早期他們以家族的形式表演夏威夷最真實、「傳統」的吉他演奏與歌舞,之後他們到全世界旅行表演,有整整五十六年時間未回到夏威夷。五十六年後他們都已經八十幾歲,回到了夏威夷,此時夏威夷本地的「傳統」音樂跟 Moe 家族表演的「傳統」音樂已經很不相同。那麼到底誰是「傳統」?誰才具夏威夷性?要掙脫「傳統」、「現代」、「文化」本質性的理解與想像,克里弗德主張要從重新思考「田野」 做起。因為田野工作是人類學知識生產最重要的方法。對田野不同的定位與理解,會直接影響生產出來什麼樣的人類學知識。克里弗德主張用旅行的隱喻來鬆脫田野僵固的想像,但同時也要意識到旅行隱喻有其限制。強調用「路徑(routes)」的眼光來關照到田野過程中所有對「根源(roots)」的各種(外來)影響,看到歷史的痕跡與各 種政治經濟的推力與拉力,理解人的選擇與文化的發展是有歷史限制的。並且這些狀況已經是人類學無可逃避、必須正視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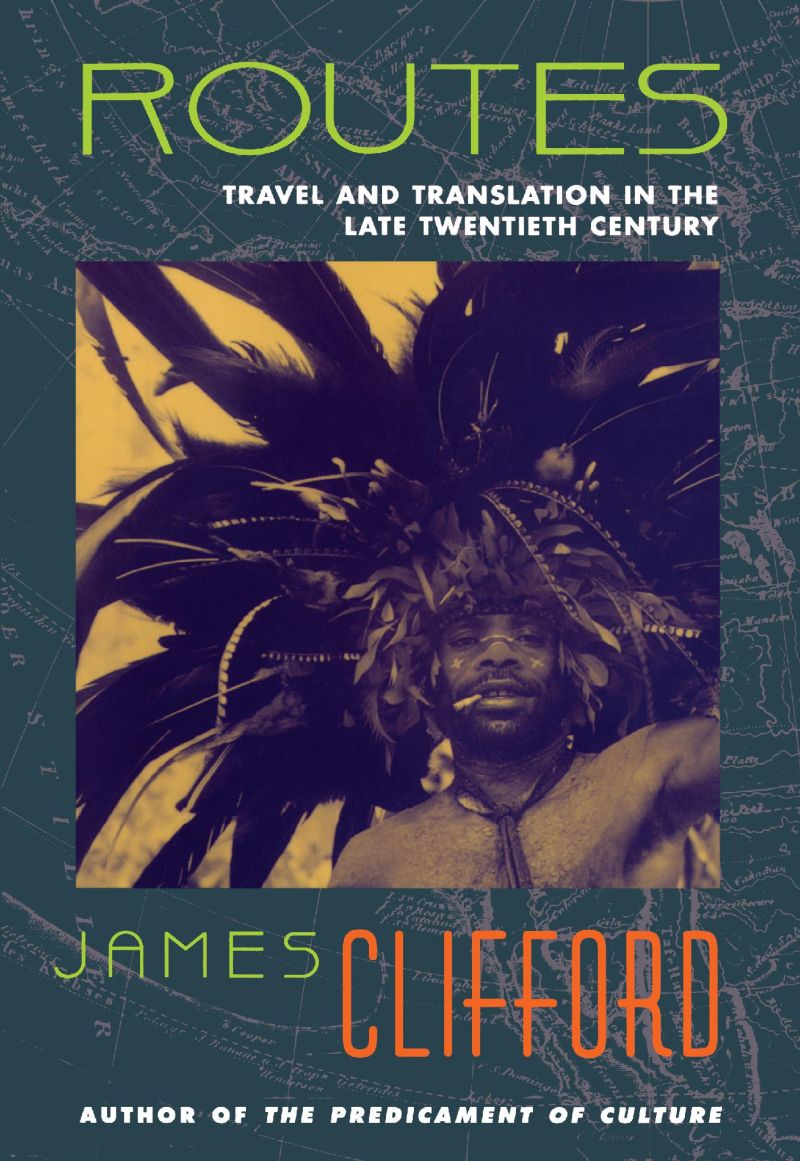
Clifford, James. Rout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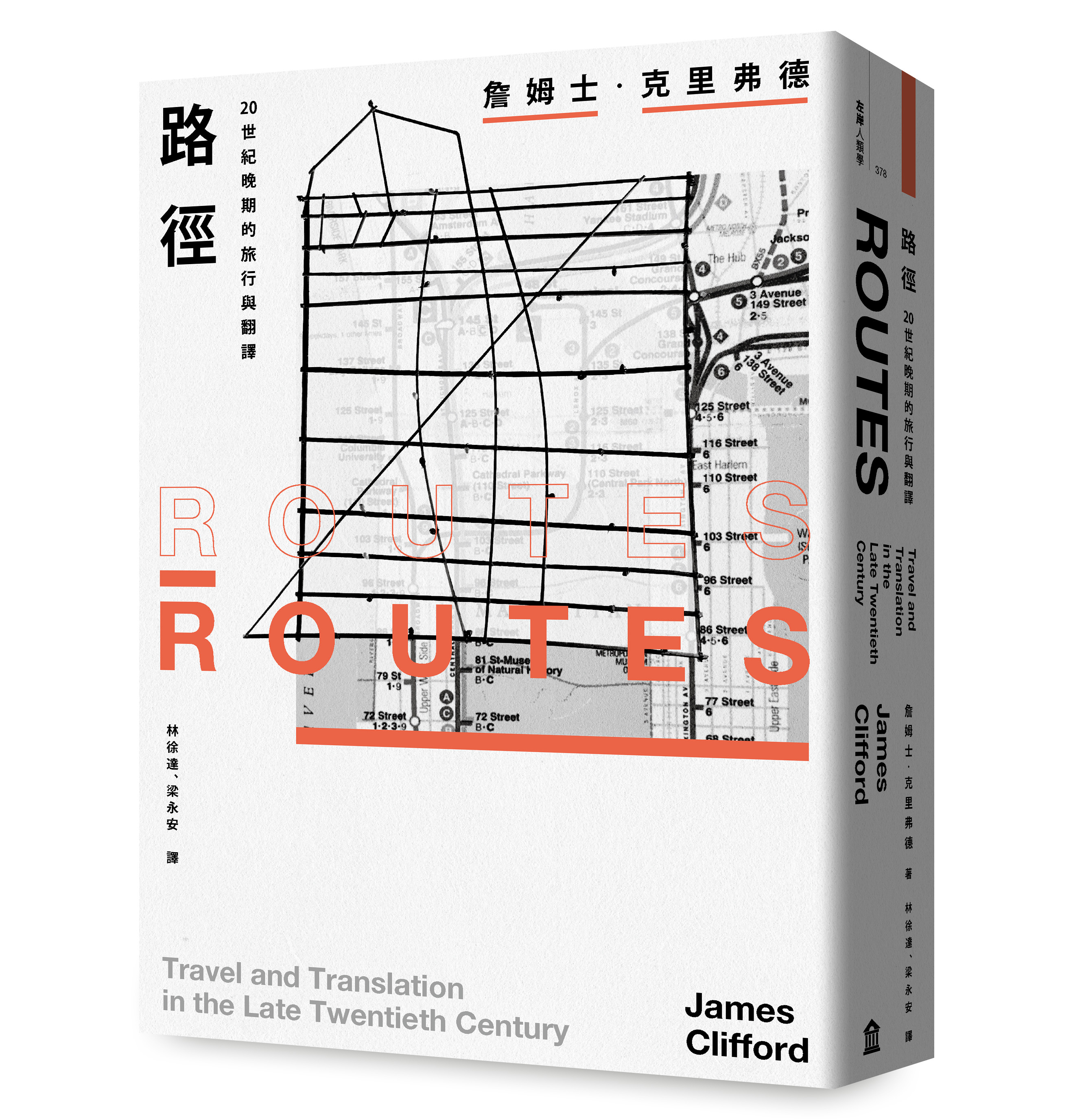
詹姆士.克里弗德,《路徑:20世紀晚期的旅行與翻譯》。林徐達、梁永安譯。左岸出版。2024。
另一個我很喜愛的例子是克里弗德在《路徑》第六章所描述一個名為「天堂」的展覽。這個展覽在英國倫敦梅非爾人類學博物館舉辦,展覽的副標是「新幾內亞高地的連續與變遷」,這個展覽毫不避 諱展現任何因為殖民、經濟作物引入、宗教變遷與物質環境改變對文化產生的質變與影響。一幅身穿傳統服的女孩相片笑得燦爛,仔細一 看,她將原來掛在前額的戽型貝換成一個鐵罐的蓋子。一條用口香糖包裝紙縫製而成的可愛小頭帶,其絢麗色彩與長期用來裝飾頭帶的羽 毛非常相像。因為商業的擴張與生產咖啡的盈餘,讓人們可以購買別的地區進口的羽毛來融入傳統服飾中,色彩更加多變與絢麗。並且「新幾內亞高地原住民普遍地把這個過程視為一種不斷變化的時尚, 而不是『傳統』的消失。」透過展示一家重建的高地貿易商店、與前殖民者探險隊的接觸、做為新娘聘金橫幅的物質變遷、變遷中的祭典與會所、傳教士帶來的影響、以及女性編織網袋的複雜演進過程, 在在以令人驚艷的方式展示新幾內亞高地變遷中的文化。在這個展覽 中,文化的衝突感並不表示缺乏文化的連貫性,而是一個更大的、複雜的秩序,透過道德跟政治領域的動態對比而標示出來。值得注意的是「天堂」展覽的目的與策略,顛覆了過往博物館的展示手法與效果,形成了溫和的反身性,並展現了豐富的意涵。用進口的天堂鳥羽毛裝飾會比用口香糖包裝紙裝飾來得「傳統」?顯然並非如此。傳統「純淨」的原住民文化受到文明「污染」,終將注定逐漸消失?看了這個展覽,感受到的顯然也不是這樣。事實上,文化並沒有所謂的本真性,文化會隨著社會的變遷而融合與再生,並且依然生猛有活力。 雖然變遷的條件並不是原住民自己可以選擇,壓迫、限制與原住民的存續同時存在。
分析完「天堂」前台的展覽,緊接著克里弗德又透過各種路徑來 分析後台如何策展。由於策展人澳韓龍( O’Hanlon)撰寫了一本精彩且鉅細彌遺的展覽專輯,引發克里弗德從新幾內亞高地歷史的脈絡、 澳韓龍與原住民的互動及文物的搜集、策展的策略與實務等等面向, 分析這個展覽是如何接觸、如何做跨文化翻譯、如何詮釋、產生了什 麼影響、以及有什麼樣的權力關係。在這裡,克里弗德示範了他如何 透過他的路徑來提出獨特的切入視角與問題意識,如何在實際的脈絡 下積極探索與挑戰舊有的思維習性來產生具啟發性的觀點。「天堂」 這個展覽最吸引人的是顛覆了人們對文化本質化的想像,在文物搜集 與接觸的過程中也清楚浮現資本主義交換的價值和美拉尼西亞交換的 價值絕然不同,但在倫敦展覽時原住民卻是完全缺席無聲的。克里弗 德細膩的提問,與各種理論對話,詳細的知識拆解與建立過程我在這 裡賣個關子,請各位自己到本書的內文裡去看。但我在這裡想針對克 里弗德所謂的「路徑」到底是什麼意思?提出更進一步的思索。
綜觀《路徑》全書,克里弗德的關懷終究是人類學的,他在某 個高度的結構性位置上,挑戰過往人類學田野工作與知識生產的規訓,指出視域必須要重新定位。克里弗德拼貼式的沈思與書寫引人入 勝,我想儘管不是人類學領域的人們也會被他「人類學凝視」的旅行 書寫所吸引,因為他展現了人類學最迷人的獨特視野。人類學這門知識已經開創並累積許多不一樣發現知識的方法,這是人類學知識生產過程中最為有趣也最為痛苦的地方,也是為什麼田野工作在人類學 學科當中這麼重要、這麼奧妙、長久居於核心地位不墜。《路徑》一書的目的正是試圖探索人類學知識生產的核心,也就是如何跨界、如 何定位。這並不是一本在第一線指導如何進行田野工作的書籍,而是克里弗德站在一定的高度上告訴你他所看到田野環境改變的趨勢,以及穿梭在田野中的各種權力結構關係,提醒人類學初學者要帶著什 麼樣的意識與敏銳度進入田野,鼓勵挑戰與顛覆過往僵固的田野想像,來創造新的人類學知識生產,並在這個過程中重新定義人類學是什麼。
人類學這門知識就是透過移置與跨界,不斷掙扎與切換於不同的 位置與認識論之間而生產出來的。克里弗德在《路徑》中指出,「原本田野工作的定義取決於透過空間的旅行與定居經驗,以及透過參與觀察者良好的訓練與具體的互動,如今被『原住民』、『後殖民』、『離散』、『邊界』、『少數族群』、『激進份子』,以及『立基社群』等學者重新改變其路線。」在這個年代,對變動中的流動性位置具有高度的敏感度,比起以往更加重要。如果過往人類學透過社會 空間隔離所建構出具本真性文化的他者,是透過根(roots)固定的差異位置所建立;當今的人類學研究則是透過路徑(routes)(包含移 動中的、抽象的)間的差異位置來建立這門知識。《路徑》一書中對「位置」和「流動性」的敏銳度與複雜意識的強調,也凸顯人們在這 樣多孔穿透與流動的文化現場中,擁有多層次與複雜的認同,而不是各自獨立的認同感。
田野工作在移置(displacement)中開始,也在移置中結束,跨越許多制訂出來的界線。但這種移動的限制與條件何在?當前的人類學的田野已不必然受到西方主導,田野旅行不見得是從歐美地區的大 都會或各國海外(殖民地)據點起始,各種不同田野旅行的路徑與經驗被開拓出來,開展出許多對不同旅行路徑的意識,「田野」的定義 也因而拓展。史碧瓦克(Spivak)以「世界化」(worlding)來說明 西方的田野旅行經驗是扎根於某種歷史視角,某些人(西方人)不斷 移動和擴張,其他人則是根深蒂固與靜止的。但是「在地人類學家」 或「原住民人類學家」的出現,活生生的打破上述的準則。他們的田 野旅行是從家∕研究地點,繞道到大學或其他提供分析和比較的場 域,再回到自己的家∕研究地點。在此,家與海外的空間化的田野地點概念是相反的。但也有些原住民人類學家的文化比較研究並不把西 方∕大學假定為理論累積的中心。儘管他們的研究可能涉及許多階層與權力關係,但他們未必依附於權力的路線,而是做不同的連結,儘管現實上學術圈仍然存在著霸權結構。
各種新的田野路徑與型態出現,帶來觀念上的挑戰,包括「家」該如何定義?「局內人」、「局外人」該如何定義?「家」是走向「田野」的出發點嗎?但對在地人類學家,所謂「走向」田野其實是「走回」自己的家。田野工作要求到其他地方,使得「家」變成起源、固定和同質的場域。但是「家」其實可能是離散、流動的,也是充滿權力關係(在性別、階級、族群、文化……等面向)的地方。民 族誌再也不是一個局外人研究局內人的規範性實務了。事實上局外人∕局內人的二元對立是起源於殖民結構,也已不適宜再如此劃分。打破家∕田野二分法的民族誌研究概念,重點在於意識到研究者進出田野所處的不同「位置」在哪裡,並且這些「位置」不是一個定點而是一條流動的路線,用一條條旅行的路徑比較容易想像。不同的「位置」必有其優勢和限制,也有其權力關係。從不同的位置移置和跨界所研究出來的人類學知識,也會有不一樣的觀點和批判產生。
在二十一世紀的東亞台灣,我身邊就有許多研究自己的「家」 的民族誌研究者,包括我自己也是。我就讀的東華大學原住民學院裡的碩、博士班學生中,有多人是繞道到大學裡頭的在地人類學家,並且各自的路徑也非常多樣,形成一個複雜的旅行網,能夠碰撞出許多有趣的想法。我認識的學弟妹有人從小就在都市出生長大,處於原住民離散的狀態,在早期台灣普遍歧視原住民的社會氛圍中,他們也不 見得認同或了解自己的身分與部落文化。但在自己長大與讀大學的過程中,從各種管道受到原住民意識的啟發,於是有很多人展開自己的原住民身分追尋之旅。許多人返回部落重新學習自己的族群語言與文化,學習部落的倫理與價值,重新找回自己的「家」。就讀研究所後,他們選擇以自己原鄉部落為「田野」做研究,學習做一個在地人類學家,也學習成為一個堂堂正正的原住民。而且,我博士班的學長姊、學弟妹中,有許多在地人類學家不只是在部落做研究,也透過各種實踐在為部落找出路,包括我自己也是。我們有一群在各自部落實踐的博士生,因為關心原住民共同的處境與未來發展,組成一個讀書會,共同閱讀與討論相關書籍,並不定期視訊交換對時事、知識或部落事務的看法。我們時常奔波在部落、大學與各自工作場所之間,並為了部落事務勞心勞力,有時也會感到心力交瘁。但我們彼此鼓勵、 互相打氣,激勵彼此莫忘初衷,能夠成為一個能為原住民部落打陣地戰的有機知識份子。
我自己也是一個典型的有複雜旅行路線的人類學家。我在原住民部落研究我的鄰居,但我並不是從小在這個部落出生、長大的原住民,而是與部落夥伴共同推動部落工作長達二十餘年的漢人女性,後來因緣際會也嫁入這個部落,成為阿美族奇美部落的媳婦(Kadafu)。我的博士論文題目就是我長期與部落夥伴共同推動的部 落合作經濟。因為長期推動部落事務,我時常被要求代表部落參與各 種會議,甚至代表部落發言。我超抗拒成為別的學者的報導人,但不知為何總有許多學者專家喜歡找我當報導人,此時我心裡總有許多OS:「為何部落那麼多人,偏偏要找我當報導人?為何部落觀點要從我來看?」我在部落推動部落事務也做研究,我觀察我的夥伴與鄰居,同時也被觀察、被監視、被要求,並且期待與勉勵我要扮演保護部落、爭取部落最大利益的那個人。這種責任與壓力已超越一個人類學家所該承受。但我本來就不僅是一個人類學家,我也是一個部落工作者,一個被部落族人賦予要求與責任的部落孩子。我的身分與旅行路線對我的人類學研究工作自然有其優勢,但也有其限制。我也期待能夠從我獨特的旅行視角,提出知識上特別的貢獻。
正如古塔和弗格森所指出,人類學的研究應該將焦點放在「shifting locations」(轉移定位)而非「bounded fields」(框住田野)。即便是原住民人類學家被視為局內人,但「沒有任何人可以在社群的所有面向都成為局內人」,仍然有可能去找出不同的定位,去 做田野差異位置的詮釋。「轉移定位」並非指傳統上對空間的定義,而是一種有意識的研究策略,不能與以往人類學田野那種對立的相遇中的定位相混淆(「這裡」和「那裡」、「我們」和「他們」、「我們的社會」和「他們的社會」)。轉移「定位」是在特定的「接觸區域」(contact zone)協商邊界與跨越邊界,但此邊界並不是絕對的, 可以被其他協商的邊界或互信關係跨越。例如一個中產階級的研究者 去研究工人階級的性別關係,研究者的階級依然扮演重要的角色。克 里弗德也指出,「沒有任何一種定位是可以選擇的,這些定位都會因 為歷史與政治性的環境而加在你的身上。由於定位本身就是多重的、 同時發生的與跨界的,因此無法保證會有共享的觀點、經驗或團結 性」(本書頁24)。認知並承認民族誌的政治面向,各種位置都是一 樣偏頗和被定位的,現在沒有任何保證安全或道德上無懈可擊的立足 點。過去民族誌被認為是研究者和研究主體建立互信關係來開展研究 的可能,如今看起來更像是建立一種聯盟關係。克里弗德認為定位的 轉移,必須正式列入人類學研究方法的訓練當中。
但這只是閱讀《路徑》的其中一種解讀。克里弗德書寫《路徑》 的方式是非常拼貼的,他透過自己旅行在大量的民族誌裡、旅行在理論中、旅行在博物館、旅行在世界文化遺址、旅行在原住民地區混 雜的歷史與殖民背景,不斷的沈思與提問。我認為,克里弗德最厲害的地方就是他很會問問題,並因而引發很多思考與遐想。在這個過程(路徑)當中,他也不見得提出了什麼解答,但作者透過旅行的交遇不斷的在找路。閱讀《路徑》的讀者,說實話其實還蠻容易迷路的, 因為克里弗德並沒有打算提出簡單的答案,也或許他自己也不清楚真正的答案是什麼。但這個世界其實就是這樣複雜,人類學的訓練就是要能看穿事物複雜的本質,並要有能耐將表面理所當然、自以為是的思考框架打破,指出事情就是這麼複雜,沒有那麼簡單,或許我們可以找出更好的看待世界的方法。所以,能夠問一個好問題是重要的。當我為《路徑》中文版書寫這篇導讀時,距離一九九七年克里弗德出版此書時已經有整整二十年。二十年後重新閱讀這本書,許多當初克里弗德在書中質問與力圖鬆脫的概念,現在讀起來仍具啟發性。這是一本能吸引許多人閱讀的書,沒有人類學背景的人可以透過克里弗德獨特的視角,以新的眼光重新去看待這個世界;受人類學訓練的學徒,建議帶著自己的閱讀策略來看這本書,畢竟專業人類學領域在這二十年間已獲得更多的進展,我們可以在《路徑》的基礎上走得更遠,並且學會在自己的路徑上去提出一個又一個好問題。
最後,我想提出一個例子,來和《路徑》書中一開始就出場的印度裔人類學者高緒的旅行經驗做比較。二○一七年夏天,我和奇美部落的夥伴們組團到南美洲秘魯,去觀摩當地原住民的公平旅遊、農業 合作社、以及手工藝合作社。在這趟旅程中,我們是帶著目的去的,因為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我們希望能為奇美部落正在進行的合作經濟 帶回來一些新的想法。我們沿路都和一般的觀光客很不一樣,一直很深入的在問當地原住民或是帶隊導遊很多問題,常常把他們問倒了, 因為我們深入挖掘了許多超乎他們一般準備範圍內的問題。在旅行的空檔,我們奇美部落的夥伴會聚集在民宿客廳或旅館房間內討論我們一路的所見所聞與收穫。我發現,在我們相互補充與分享各自問到,或事前做功課知道的秘魯原住民的歷史文化背景與政治經濟脈絡後,我們奇美部落的夥伴都很有能力能看穿與分析旅遊過程中,在地原住民在前台沒有告訴我們(或許也不願意告訴我們),可是他們後台的旅遊操作及合作運作是什麼。因為我們奇美部落的夥伴們,同樣也在全球資本主義的壓力下,以及殖民歷史的背景下,試圖復振部落文化與發展原住民團結經濟。這一路的跌跌撞撞與不斷摸索,我們自己也親身經歷過並不斷的實作操演,並且一樣也不會秀在前台給外人看。所以,秘魯原住民的後台運作,對奇美部落的族人而言是很容易看懂的。
不同於印度裔的高緒發現他和埃及的伊馬目(Imam,亦即禮拜的導師,伊斯蘭教集體禮拜時站在眾人前面率眾禮拜者)之間,儘管彼此有巨大的鴻溝,但在一次劇烈爭吵中,高緒領悟到其實透過「西方」他們非常了解彼此,也很相像,因為他們都是經常旅行於「西方」的人。原本高緒希望透過印度與埃及的連結,突破東∕西、帝國∕殖民、發展∕落後的思維論述,來發展他的民族誌。然而當他發現他只能在「西方」找到伊馬目時,他的希望就此破滅。一九九二年高緒在《伊馬目與印度人》書中,紀錄與分析了印度與埃及兩個相對於西方現代化的前殖民地人們的接觸路徑,並提出批判。二○一七年奇美部落的秘魯觀摩之旅,東亞台灣與南美祕魯的原住民接觸路徑,展現了和高緒與伊馬目很不同的移動路線。台灣與秘魯的原住民並不是非得透過「西方」的思維與經歷才能連結彼此。相反的,因為有相似的被殖民經驗,以及同樣在全球資本主義巨大壓力下 被迫離散求生存的處境。並且,兩地原住民都試圖復振與保存自己的文化,及發展部落團結經濟。這些原民復返的經歷,讓奇美部落族人 發現,儘管秘魯原住民的語言、文化和生活環境都跟我們有巨大的不 同,但其實我們很相像,且我們很容易了解對方。
看到這裡,你是不是也很想試試看這種用路徑來思考的方式,來發現一些新的看待世界的方法?邀請你一起來閱讀《路徑》這本書, 並提出更多不一樣的解讀,開發更多開創性的視角,積極探索與顛覆對這個世界原本受限的想像。而這,就是人類學發現知識的方法。
參考文獻
Appadurai, Arjun 1988 “Putting Hierarchy in Its Place,”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3 No.1:36-49.
Clifford, James 1997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Returns: Becoming Indigenou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abian, Johannes 1983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Geertz, Clifford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 After the Fact: Two Countries, Four Decades, One Anthropologi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upta, Akhil and James Ferguson 1997 “Discipline and Practice: ‘The Field’ as Site, Method, and Location in Anthropology,” in Anthropological Locations: Boundaries and Grounds of a Field Science, pp1-4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Beyond ‘Culture’: Space,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in Culture, Power, Place: Explorations in Critical Anthropology, pp33-51.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吳明季 原住民的根源與路徑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index.php/article/7045 )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