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山林」帶回小林
用身體尋回族群技藝/記憶的大武壠族人
我想,大多數人和我一樣,是在十年前小林村被莫拉克風災的土石流無情掩埋之後,才從電視新聞裡看見、知道了「小林」。
我作台灣原住民研究,但長期以來對於平埔族群的認識卻一直侷限在文獻的閱讀,直到人類所有一位西拉雅族文史工作者段洪坤入學後,「平埔」和「西拉雅」對我才開始逐漸有了不同的意義。那一年我擔任洪坤他們班的導師,同時開始在學校的原住民中心協助相關事務,但是卻常常忘記他也是原住民,這時洪坤總會幽默地表達抗議,讓我驚覺自己在潛意識裡和一般大眾一樣,有著「平埔」已然「漢化」的刻板印象。2009年莫拉克重創小林,風災過後的兩個月,我得知小林村仍決定照常舉行夜祭之後,詢問洪坤是否可以幫忙安排前往,當時他正為協助小林重建工作忙得焦頭爛額,但依然一口答應了我的不情之請。儘管只是短短兩天一夜的行程,從小林夜祭、六重溪夜祭,到夜宿吉貝耍部落,「西拉雅」族人的祭儀、器物的美感,以及強韌的生命力深深烙印在心底,我再也不會忘記他們是台灣的原住民。
數年後因為原民會的「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我再次見到小林村人,並且聽見了他們希冀正名為「大武壠族」的堅持。雖然我主要執行的是原民活力計畫(註一),但偶而也會應邀參與平埔活力計畫的評鑑。尤其近幾年來,兩個活力計畫在年底共同舉辦成果展,讓從不缺席的我因此能稍稍瞭解各個平埔聚落的營造內容。儘管在平埔活力計畫的官方語言中,他們只能被稱為「聚落」而非「部落」,也無法像原民活力計畫能執行產業的面向,但因為珍惜這個得來不易的機會,平埔各聚落之文化復振的努力與成果讓人格外動容,也因此轉變了不少參與活力部落之原住民既有對於「平埔」的漢化刻板印象。其中,日光小林聚落的成果又特別讓人驚艷,他們不僅成立了有能量四處巡演的大滿舞團、還正式出版了兩本非常紮實豐富的文化書:《種回小林村的記憶:大武壠族民族植物暨部落傳承 400 年人文誌》和《用手說的故事:小林村大武壠族部落工藝人文誌》。而之所以這麼賣力拼搏的原因,正是因為在那場風災中,小林村人已然失去了太多。
在上述片片斷斷的互動過程中,我逐漸體會了這些過往被泛稱為「平埔族」的族人們心裡難以言喻的艱難。他們所要面對、承擔的不只是漢人的歧視(你們的長相一看就是「番」)、「漢化」的不當污名(你們的語言文化都消失了)、法定原住民的不理解甚至誤解(你們祖先當年放棄當原住民,現在卻要來瓜分資源),更難的是歷代殖民政府有關「高山」和「平埔」之不同政策所造成的認同混沌(我究竟是漢人還是原住民)。
從「平埔」到「西拉雅」到「大武壠」
不管是二、三十歲的青年或年已七十的長輩,小林村人過去大多不知道自己是原住民,直到1980年代有人來到村子裡做研究,以及1996年小林村重新舉辦所謂的「平埔夜祭」,才聽外面來的學者說村民是「平埔番」或「西拉雅族」。但因為不被政府認定是「原住民」,小林村人對於自己的族群身份大多還是懵懵懂懂,直到莫拉克風災後,面臨親人驟然離世、族群瀕臨消失的生存危機,族人才驚覺到原來一場天災可以一瞬間把所有的文化帶走,於是年輕人回來,開始從文獻資料裡去追問自己究竟是誰,進而找回了「大武壠族」的認同。
早期學者將「大武壠」視為西拉雅族的分支,但日治時期學者小川尚義收集到西拉雅和大武壠在用詞上有許多不同,之後語言學家土田茲和李壬癸更根據語言學上的研究將大武壠和西拉雅分為不同的兩個族。大武壠人原居居於台南玉井盆地一帶,被稱做「四社熟番」,包含了大武壠頭社、霄里社、芒仔芒社以及茄拔社四社。後因荷蘭人、漢人陸續開墾侵占土地,入侵西拉雅族部落,進而輾轉壓迫到大武壠族的生活。乾隆年間,一些大武壠頭社群的族人開始遷徙至楠梓仙溪一帶,後清朝政府在阿里關設關隘作為漢人與山上原住民間之緩衝,於是有東阿里關(現高雄市甲仙區關山里阿里關)之大武壠族人隨清朝開山軍隊往那瑪夏方向拓墾。到了日治時期,日本人為開發山林樟腦將這些散居的族人聚集於派出所附近,形成了「小林」這個大武壠族最大且最晚成立之部落。

莫拉克風災後,按照政府原先的規劃,小林村民與其他區域的災民一起被安排在杉林的永久屋區(今杉林大愛村),無法保有獨立的社區空間。許多族人對此不能接受,堅持小林村必須獨立重建,但對於遷居地點有不同看法。有人想重回甲仙五里埔舊址,就近原地重建;有人卻因為不想重返傷心地、距離工作地點較近等因素而希望移居杉林,只是不想與其他災民一起混居。
最終,小林村人分居於三處的永久屋。66戶入住杉林大愛,但居住在相對獨立的區域,自稱「小林小愛」村;五里埔的永久屋有90戶為「小林一村」;而主張自主重建,亦即希望按照記憶中的印象,盡力重現小林村面貌的120戶小林族人,則在2011年年底入住杉林的「日光小林」永久屋,被稱做「小林二村」。
從療癒之中長出力量的大滿舞團 (註二)
在組合屋時期,日光小林的多名婆婆媽媽跟著會做麵包的返鄉青年王民亮成立烘培坊。然而阿亮發現,產業似乎不是族人最迫切需要的,村民依舊活在沉重的傷痛之中。他想起小時候參加村裡的夜祭時,村民一起唱歌跳舞的時候很開心歡樂,於是成立了舞團,想要藉由唱唱跳跳找回大家臉上的歡笑。舞團的首場秀,就是在日光小林永久屋的入住儀式上表演,找隔壁大愛永久屋的原住民朋友來教,跳的是阿美恰恰。後來開始有外面的邀約,跳別人的舞越跳越心虛,身為舞團團長的阿亮覺得,應該要慢慢找出屬於自己族群或部落的東西,於是回想以前媽媽們工作的姿態與動作,編進舞蹈之中,同時也請外來的老師幫忙把小林的故事編成舞碼演出。剛開始練舞時,團員經常因觸景傷情哭成一團,但漸漸的一起唱歌跳舞成了最好的集體療鬱方式,族人透過唱歌的方式和家人聯繫,思念家人,只要唱起歌的時候,就知道家人在他們的身邊。
莫拉克風災時,日本友人隨著善款贈送向日葵種子,希望小林人能如向日葵一般充滿陽光歡笑,「日光小林」這個名字即源於此。因此2011年日本發生311大地震,小林村民感同身受,雖然財力很弱,仍在第一時間捐助50幾萬元送愛到日本,並且將赴日本 311 災區義演定為長期目標,希望同樣以自己的故事為日本災民打氣,以舞蹈撫慰他們。
2014年,大滿舞團終於如願赴日演出,同時驚喜的找回了1930年代日本學者紀錄下的大武櫳古調音檔,回台之後,阿亮帶著大家土法煉鋼,一個字一個字模仿裡頭的聲調和發音,克服了許多挫折和難關之後,團員們的歌舞越來越有力量,也越來越貼近文化。
為了莫拉克拉克風災十周年,2019年大滿舞團推出名為「回家跳舞」的巡迴演出計畫,將祭儀與大武壠族古謠結合呈現。巡迴音樂會的曲目有1930年代由日本人類學家淺井惠倫所採集的古謠,也有這兩年部落耆老所採集到的古謠。團長阿亮說:「無論我們在哪裡跳,其實都是為了跳給天上的家人看。」

跟著獵人的步伐
然而,即使一起唱歌跳舞讓族人逐漸走出傷痛,療癒自己也帶給別人感動的力量,但永久屋仍然不那麼像「家」。
2015年開始,日光小林開始推動「大武壠歌舞文化節」,以及和 《Mata Taiwan》 合作兩天一夜的部落深度文化小旅行。也就是在這一年,阿亮的堂弟,一樣在風災之中父母俱逝,即刻辭掉原本在北部工作住進組合屋的大駿,接下了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計畫的部落營造員職務。
大駿說,一開始參與社區活動帶所謂的「部落導覽」向外來訪客介紹永久屋時,總是覺得很心虛。因為永久屋和從前小林村被山林環繞的環境完全不一樣,除了房子什麼都沒有。他覺得每次來參觀的人都好像在看猴子,帶導覽時,聽到人家說你們住的房子很好很漂亮時,也感到格外諷刺。因此,當大駿接下平埔活力計畫作田野調查,從耆老口述裡驚喜地蒐集到不少有關植物的族語時,突然有了這樣的想法--何不把這些負載著文化意涵的植物從老家附近的山裡,移植到永久屋來?
由於小林村世代在山林與河川之間定居,前有楠梓仙溪,後有獻肚山,對岸的奚阿里關山也是獵場,族人對於漁、獵並不陌生。當大駿不只想要紀錄下長輩口中的植物和相關知識,而是要實際把這些民族植物種在日光小林時,身旁的徐大林和徐吉綠兩位耆老成了他最為仰賴的導師。他跟著兩位獵人進入山林,小心翼翼地把過去記憶中族人會使用的植物移植到永久屋,先用盆栽養活,然後種在前後院裡,並且進一步規劃成「日常生活」和「傳統文化祭祀」兩個植物園區。
日常生活植物園區包含了大駿記憶中孩提時期拿來做零食的虎婆刺(山上野草梅)和種子可做竹槍子彈的土密樹,長輩們在山上會食用的破布烏,以及會拿它的葉子來煮肉湯的山柚等;傳統文化祭祀植物園區則是包含了和公廨以及祭典相關,如製作花環的植物等。雖然夜祭在小林村曾經中斷多年直至1996年才重新舉行,公廨與太祖信仰卻始終存在於族人的日常生活當中,不曾消失。莫拉克風災後,每年農曆九月十五日在五里埔小林公廨舉行的夜祭,更是成為凝聚分居三地之小林大武壠族人重要的信仰力量。
透過這些移植到永久屋的民族植物,如今大駿得以在導覽時很有底氣和自信的把遊客「帶回」小林村以前的生活,除此之外,2017年他主編、出版了《種回小林村的記憶:大武壠族民族植物暨部落傳承 400 年人文誌》一書,細緻地以蒐集到的民族植物知識為引,對於小林村的歷史、信仰、飲食和山林生活做了相當精要的概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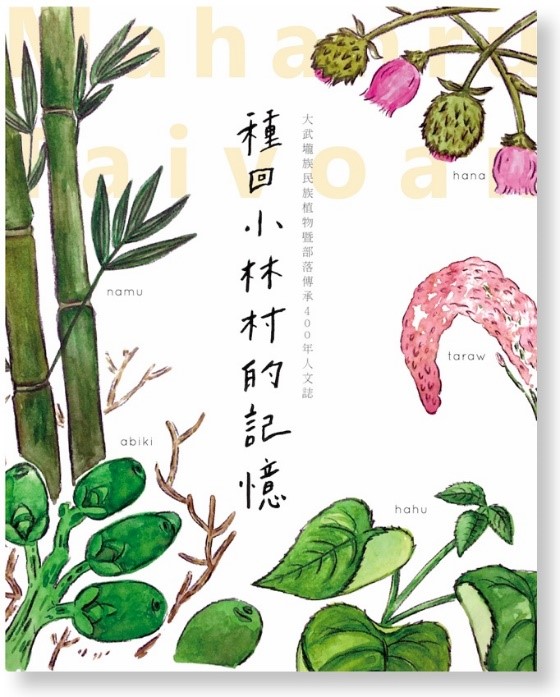
而帶著大駿走入山林的徐大林和徐吉綠兩位耆老不只是獵人,也是手藝精巧的工藝師。吉綠阿伯精美的「魚笱」、大林阿伯製作的會自己把魚釣起來的「漁釣」,以及兩人的生命史,均成為隔年出版的《用手說的故事:小林村大武壠族部落工藝人文誌》一書中的重要素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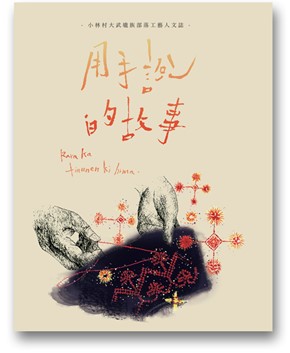
讓刺繡成為回家的路
在《用手說的故事》一書的序言中,大駿特別感謝了此書出版前剛剛離世的台大人類學系胡家瑜教授。莫拉克風災後,胡老師和高雄市歷史博物館共同參與了小林村重建計劃,於2004年出版《針線下的繽紛:大武壠平埔衣飾與刺繡藏品圖錄》一書。大駿看到書裡祖先如此精湛的刺繡技術後,趕緊拍照傳給潘燕玉研究,原本就喜愛西洋十字繡的潘燕玉自己按圖摸索,成功地復刻圖樣,自此開啟了部落找回大武壠傳統繡法之路。2018年,日光小林與台東卡塔文化工作室合作,由潘燕玉和另外一位更年輕的族人劉怡君兩人包辦所有的手繡圖紋,完成了兩套大武壠族的女性傳統服飾,成為日光小林平埔活力聚落計畫最後一年裡令眾人驚艷的成果。

在研究早期部落老人家留下的傳統服飾物件時,大駿和潘愛玉發現甲仙一帶大武壠圖紋中,最特別的是一種如煙火般的針狀花球繡紋,族人推測這形狀應該是取自雞角刺花或是圓仔花。

資料來源:「看見小林」粉絲頁(http://www.taivoan.org/?p=47)
雖然這個圖紋究竟是何者目前尚無定論,但同為日光小林刺繡班成員的小林村青年潘家樺認為,就把它當成雞角刺花吧,因為雞角刺是和小林日常生活文化密切相關的一種特殊食材。過去小林村只有野生的「華薊」,也就是雞角刺,族人喜愛它的香味,上山工作若看到都會摘幾株回來煮雞湯給家人補一下,尤其是婦女做月子,更是一定要喝。家樺生下老大後,她的第一個刺繡作品就是把她心中珍視的這個特殊族群圖紋繡在女兒小牛仔褲的口袋上,受到眾人好評後,又把它繡在女兒的布鞋上。她說,如果小林村還在,那女兒就會是在小林奔跑的孩子,而不是在馬路奔跑的孩子。為了要讓孩子能更親近大武壠文化,儘管常常刺到手指頭都是血,家樺仍然想讓孩子能把「文化」穿在腳上,彌補孩子無法在小林奔跑的缺憾。

資料來源:「看見小林」粉絲頁(http://www.taivoan.org/?p=47)
如何讓永久屋真正「永久」?
十年前的莫拉克風災震驚全台,慈濟基金會率先提出替災民蓋「永久屋」的重建方向,希望能在平地造村,並以放棄山上家屋作為條件,讓山區居民永久下山、遠離災害。但對許多居民來說,到目前為止,山下都還只是一處據點,還未能完全取代山上的家。這場「永久」與「臨時」的戰爭,在人、山與平地之間,來回拉扯了十年。
何欣潔、趙安平: <災後平地造村記:一場「永久」與「臨時」的戰爭>
莫拉克風災已經經過了十年,當年未經深思熟慮、急著想一步到位的永久屋政策,造成了許多現實和文化上的生存問題,沒有耕地、房屋無法隨著人口增長擴張、改建,如何讓永久屋真正「永久」至今依然是個待解的難題。
對日光小林的大武壠族人來說,面對「在永久屋裡想家」的困境,他們的解決方法之一,便是跟著耆老的手藝和腳蹤,透過身體的實踐,把「山林」重新帶回到這個只有房子的基地。在一個訪談中大駿這樣說:
我對於永久屋的想像是,我希望我們以後的永久屋,它是人跟土地的關係,是緊密扣在一起的,因為土地可以延伸出很多植物的生命,我們的狩獵文化、我們傳統的工藝文化,都是從土地延伸出來,不是憑空出現的。因為以前我們都是用所謂的自然材質在使用的一個文化,我希望以後的日光小林可以呈現出一個大型植物園,他和部落是緊密扣連在一起的,那才是我想要大家體驗的小林村。
風災過後,許多倖存的小林村人常常會問自己:「為什麼是我被留下來?」,經過這些年,終於得到了答案。是文化,讓他們找到了留下來的理由。
註一:2009年,我開始參與「原住民族部落永續發展實施計畫」,2012年原民會將此計畫更名為「原住民部落活力計畫」,同時因應平埔族群日益迫切的文化復振需求,啟動了「平埔族群聚落活力試辦計畫」,並於2014年將之轉為正式的五年期計畫。
註二:舞團的名字「大滿」是為了紀念莫拉克風災時的小林村公廨,當時招牌上寫的就是「大滿族小林公廨」。「大滿」來自某些大武壠族部落的自稱:Taivoan,因此大武壠族又稱為大滿族,所釀的酒也稱為「大滿酒」。根據文獻記載,「大武壠」一詞最早出現在 17 世紀初,記錄於《台灣略記》裡,指的是位於現今台南玉井的 Tavorang,即「大武壠社」,而某些部落族人的自稱 Taivoan「大滿」,可能是「大武壠」的音變。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邱韻芳 把「山林」帶回小林:用身體尋回族群技藝/記憶的大武壠族人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767 )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發表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