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側》導讀
活著的殘酷
《生命之側》(Life Beside Itself: Imagining Care in the Canadian Arctic)成書於二○一四年,是作者麗莎.史蒂文森博士論文所改寫的作品。史蒂文森從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取得人類學博士後,在哈佛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並在那個階段開始思考如何將博士論文進行改寫。因受到後殖民概念的影響,史蒂文森將本書的基調定調於加拿大政府對原住民的健康治理政策的批判反省。除了完成此書,史蒂文森亦拍攝了一支紀錄片《進入未知的部分》(Into Unknown Parts),在二○一七年的瑪格麗特.米德電影節播映,內容正是本書的一部分,陳述因紐特人被迫離開家鄉的社群,在南部結核病療養院生活的經歷。加拿大政府那個階段的結核病照護政策,也讓作者進一步思考其對因紐特社群所實施的自殺防治的問題。本書所挑戰的,是當今在一種科學理性下所定義的「生命」,並且對當代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治理性」(governmentality)提出批判。雖然中文版距離原書出版已有十年,但對當今原住民健康照護仍是相當即時的提醒。

《生命之側:關於因紐特人,以及一種照護方式的想像》(Life Beside Itself: Imagining Care in the Canadian Arctic)
論及族群與健康,「健康不平等」已成為當代公共衛生與批判醫療人類學(critical medical anthropology)的關鍵字。但所謂的「不平等」,在全球發展的歷史上並不是一件陌生的事。如果將視野縱深拉長,全球社會約莫在二戰後就開始討論不平等的發展,也透過國際組織與地方行動企圖弭平疾病,從二十世紀下半葉至今,國際醫療與全球健康的行動可謂前仆後繼,在世界各地有著許多值得省思的案例,也有許多介入方式的變化。舉例來說,世界衛生組織天花疫苗的施打,在一九五○至七○年代帶來斐然的防疫成效,同樣的模式卻無法有效地抵抗麻疹。這個過程,迫使人們必須反省那種企圖由上而下,並尋求單一科學技術應用於各地來畢其功於一役的可能性。相對地,一九七八年的《阿瑪阿塔宣言》(Declaration of Alma-Ata),則強調了需要有一種因地制宜的健康介入方式,成為當今我們看待全球健康的方針。
從這樣的歷史過程來看,我們就會發現,類似的狀況在全球社會仍持續發生。面對疾病,有時一些看似殘酷而不合人道的處理方式,或許是因為科學技術的缺乏使然。但即使技術逐漸成熟,影響健康治理的因素,仍有千絲萬縷政治經濟與文化因素牽扯其中。《生命之側》正是一本對健康介入提出反省的民族誌。它的書寫方式相當特殊,其一是它所論述的對象。作者明言,本書所凝視的對象是「照護」(care),但其所謂的照護,並非當代醫療中的照護行為,也不一定是那種存乎於傳統社會的特殊照護方法。史蒂文森的書寫策略是以一種打破直觀的,以語言、行為為主的記述方式,透過「意象」(image),透過因紐特人的命名哲學、對時間的特殊感受,透過歌謠等等,來回答所謂「生命是什麼」。
兩種流行病的治理
以助人與利他為基礎的健康治理,有可能反而帶來傷害嗎?《生命之側》透過兩段流行病的治理經驗來陳述本書的要旨:「生命政治下的照護形式雖然努力維持因紐特人的實體生命,卻也可能暴露了加拿大政府的冷漠無情。」它所記述的是在加拿大原住民社群中,發生在二十世紀兩個時期的流行病,分別是一九四○和六○年代間的結核病與一九八○年後的自殺潮。
故事從一封安娜追尋父親的祖母考雅克的電子郵件開啟。原來一九五○年起,有數以千計的因紐特結核病感染者被加拿大政府直接送往國境之南,粗暴地將他們帶離原本的生活社群,以船隻載往遠方。在這段書寫中,史蒂文森透過檔案,重現當時那些失去家人的因紐特人的反應。他們有人終其一生在岸邊碼頭引頸企盼,過著一種明知沒有結果的等待。在錄音檔案裡,感染者的家屬蒼白而躊躇的問候,反應了那種壓抑悲痛而又不得不接受的情緒。這種將感染者驅離的照護方式,明顯體現了殖民者將因紐特人當作是「不健康的他者」,不顧他人感受的粗暴介入,表面上將病原體區隔開來,「淨化」社群的居住環境,卻反而帶來集體的心理創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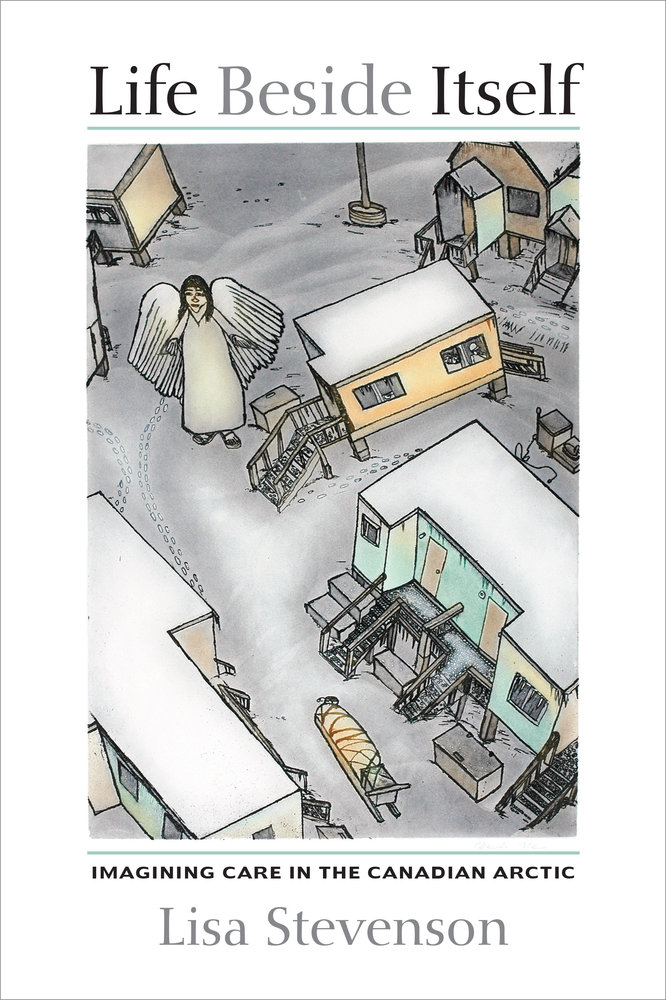
Stevenson, Lisa. Life beside itsel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
同樣地,一九八○年後日益嚴重的自殺潮,也使得加拿大政府不得不祭出自殺防治的政策,而當時殖民政府挪用了一九五○年代在倫敦創設的自殺防治專線,透過志工關懷員在電話那頭以匿名的方式提供關心。然而,在因紐特人看來,這卻像是一種「不管你是誰,只要你活著就可以」那樣粗暴的照護體制。對因紐特人來說,死亡並非生命的終結,而是生命的一部分。史蒂文森將因紐特人這種把死亡看作生命的一部分,並且認真把死者放在心上的方式,稱作「死活相依」(living mournfully)的態度。
「匿名」邏輯本身與因紐特人的命名文化是違背的。書中,作者以她的重要報導人席拉為例,說明了她與她的家人們的名字是如何同時有著生命與靈魂的意義。對因紐特人來說,他們是沒有祕密的,他們必須知道是誰在照顧誰。在這個前提之下,因紐特人的生命會透過他們特殊的命名邏輯,在死亡之後仍得以延續下去。又例如「成為安妮」這一小節,記錄了因紐特人在受到傳教士命名而遭受同化的過程中,如何經驗了「另一種消失」。史蒂文森認為,生命線擱置了一個生命的具體細節,使得生命的獨特性不再重要。名字本身是有生命的這一點凸顯了匿名專線的荒謬性。
不健康的他者
看了上述兩個流行病所反映的政策困境,可能會有一種感覺,就是當今的防疫或健康照護形式,好像不斷地在重蹈覆轍。事實上確實如此。當前健康照護的規模尺度早已不是發生在單一小眾的群體之中,而往往是以「政府」作為照護的基本行動者。人們在國家的治理下,有了「公民」的身分,因而維持身體健康,並且確保生命之存在,也就同時成為兩端—「公民」與「國家」—的基本責任,這就是當代健康公民性(health citizenship)的特點。在國家的治理下,人民似乎有責任配合公共政策,以維持社會能夠穩定而順利的運作。本書要說的就是,被治理的人如何「配合」治理的政策。然而人不會只有「公民」一種身分。如果熟悉人類學的理論,便知人類社會有其特殊的階序與文化,人們對生命也各有其特殊的邏輯。生命治理本身也可能會與地方文化產生衝突,更進一步說,以善意包裝的治理本身也可能是一種暴力。
從現代醫療的觀點來看,所謂的生命,大概就是以生命徵象為主要的量測對象,從呼吸、心跳、血壓,到腦神經活動,大致成為現代醫療判斷生命是否還存在的基礎。所謂的健康,也往往帶著與病原對抗、排除的目標。在醫療照護或公共衛生的領域,對於疾病與失能者,往往需要官僚體制與醫療系統的介入,但那樣的體系與系統有時反而是去人性的,或與文化背道而馳,或是打擊錯誤。以台灣原住民健康議題為例,過去有許多流行病學的資料顯示原住民社群有高比例的飲酒現象,但那些以數字為基礎的介入方案,像是統計成功戒酒的人數或是酒精濃度的測量,往往導致更多部落中的汙名。
〈為什麼放兩個鐘?〉這章更是突顯了一種將特定的時間邏輯加諸於原住民的壓迫性。史蒂文森觀察到因紐特人家裡刻意擺了兩個時鐘,彷彿提醒自己必須配合管理者的各種規範。她認為我們需要另一種面對死亡與各種生命樣態的方式,甚至包括時間的節奏、態度,都需要我們破除特定的知識系統裡的主流定義與做法。她問說:「我們準備好思考另一種遵守時間的方式,卻又不會立刻把它們病理化嗎?」
其實,回顧台灣原住民的健康治理,許多場景我們並不陌生。一九五○年代台灣省政府頒布的《山地人民生活改進運動辦法》,強調部落必須揚棄「落後」的生活方式,卻使得部落被捲入現代化資本主義邏輯下的經濟困境之中。類似的案例族繁不及備載。再以當代大規模災難如八八風災為例,遷村的政策也導致了部分部落族人更加孤立無援。這些案例,在在反映了在政策中,必須以保護並尊重文化為前提。近年來台灣政府與學者開始強調「文化照護」的概念,但那究竟是什麼?
「文化安全」與「文化照護」
醫療照護中的文化衝突,往往導致醫病關係的破裂,甚至使得病況加重。一九九七年由安.法第曼所著的《惡靈抓住你,你就倒下》(The Spirit Catches You and You Fall Down)便是一則經典的案例,描述了苗族的癲癇患者黎亞在美國治療過程中所遇到的各種困境。《生命之側》則將醫病關係的層級,從醫病之間互動拉高到整個治理策略的討論。「文化」作為關鍵字,正是健康治理所需要具備的洞見。然而「文化」這個詞彙本身也是難以化約的。醫病之間的互不信任絕非單獨來自對文化的誤解,它更反映了特定族群的結構脆弱性。換言之,當我們討論文化兩字,必須迴避本質主義的思考,並放在持續變遷的背景脈絡下來看待。
以台灣為例,當今原住民的健康治理也常常高舉文化兩字。二○二三年頒布的《原住民族健康法》,特別將「文化安全」作為關鍵字入法,不但強調健康照護教育必須融入與原住民族健康相關之文化安全的概念,做法上也必須以「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為主。但什麼是原住民知識體系,什麼又是文化安全?事實上,這些看似深奧的專有名詞,往往帶給第一線的健康工作者某種困惑。
原民知識體系指的是原住民本身在其生活中運用、展演的日常智慧與實作,但這樣傳統的生活方式卻在當代或外來殖民的治理過程中逐漸丟失,進一步影響原住民社群賴以維繫的健康與安適狀態。而文化安全則是一九八○年代末起源於紐西蘭對護理實作的反省,它強調了病人在參與自身照護過程中,能夠擁有足夠的決策空間,並且在靈性、社會、身體與情緒上皆能夠確保其安適的狀態。《生命之側》這本書雖然並沒有提及這些專有名詞,卻是回應這些概念的絕佳案例。然而,正如許多人閱讀這類帶有批判意圖的作品,可能會存在著一些困惑,特別是當讀者可能無法從書中得知更好的照護方案。但在《生命之側》中,作者的目的相當清楚,唯有突破主流社會對少數族群的分類與標籤,以及想像的方式,才能做到有意義的照護,而這一切都不是一蹴可及的。
意象、精神分析、文學與歌
《生命之側》在民族誌的研究方法與書寫策略上也相當特殊。首先是以意象作為方法。所謂的意象(image)並非只是平面圖像,甚至可能是一種想像。作者企圖打破文字語言的框架,以意象代替言說,她甚至直言意象就是代表一種照護形式。我認為作者企圖尋找一種超越現代醫療與殖民語言的論述方法,而她從深刻地與因紐特人相互陪伴的過程中,感受到語言之外的溝通互動方式。因紐特人並不單純以言語作為感知、訴說生命的方式。而這也讓作者認為,人們的想像、夢境、傳唱的歌謠,都存在這一種超越言語的意象表達。
誠然,從照相技術發明以來,影像早已是人類學家的研究方式,影像紀錄在研究工具的應用上也已有許多的轉折。但我認為作者的策略是創造一種超越文字的文字。她引用班雅明的意見:「班雅明的文章對我用更普遍的意義去思考意象很有幫助,因為他沒有一定要區別視覺、聲音甚或言語的意象。事實上對班雅明來說,文字本身也可以當作一種意象。」
同時,本書大量的援引精神分析的理論與文學作品的片段。在字裡行間,我們能讀到佛洛伊德,或是南非小說家柯慈與義大利作家卡爾維諾的作品。簡單地說,我認為作者本身在書寫形式上就有一種打破傳統的企圖,並傳達一種抵抗殖民的心態。人類學研究引用精神分析的案例已相當豐富,透過這樣的方式來理解文化的象徵,或是用以解釋人的心理層面有其個人與社會的二元性。至於文學,也與精神分析類似,或許能提供民族誌資料某些互補效用的理解。例如史蒂文森提及柯慈的小說《麥可.K的生命和時代》,直言「期待殖民地居民乖乖合作,共同投入延續生命此一目標的殖民欲望,是柯慈這本小說的重點」。
雖然在民族誌作品中,直接援引大量的小說文字看似有些突兀,但這也不是沒有其他的案例。例如法國人類學家迪迪耶.法尚曾與同儕合寫〈南非暴力故事〉(Fassin et al. 2008),完全以臨摹柯慈小說結構的方式來向小說家致敬。他曾言:「社會科學家最近表達了他們對小說家或導演等小說作者的欽佩……傑出的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承認,他們發現這些作者的作品中對所探究的社會世界的描繪,比研究這些世界的學者—有時包括他們自己—所提出的描述更具吸引力、更準確、更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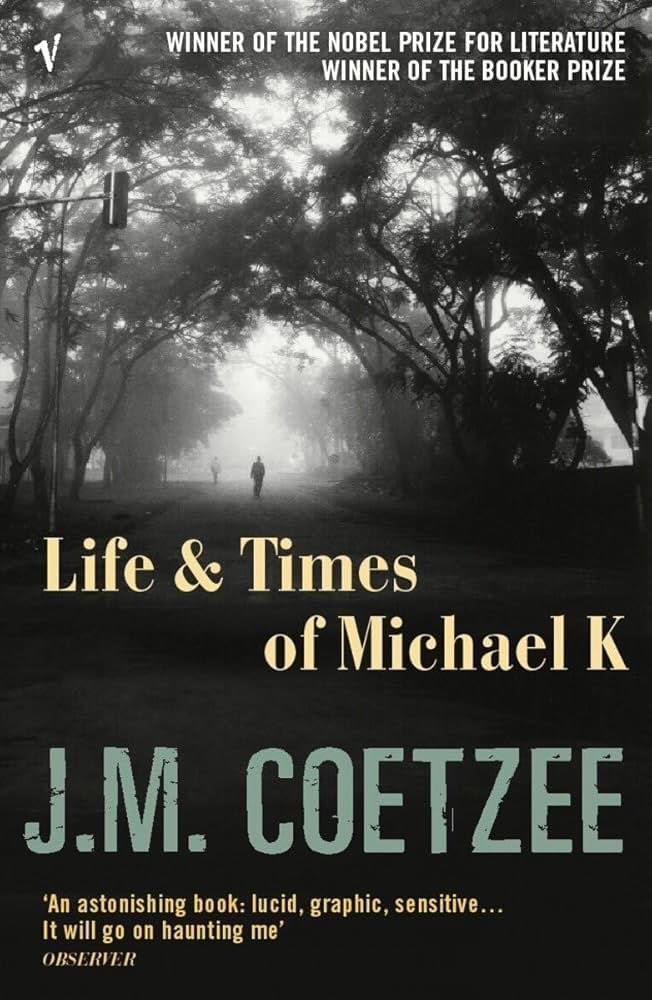
Coetzee, J. M. Life & Times of Michael K. Raven Press, 1983(柯慈《麥可.K的生命和時代》)
最後一章〈歌〉的書寫也充滿創意。史蒂文森用自己與縱火嫌疑犯保魯西的故事開場,那樣一位被看成是無時無刻憤怒的、危險的青少年,在一個營隊中唱了一首嘲笑她打獵技術的歌。音樂本身就是一種人類表達的文本,一種文化表達的形式,在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中亦不陌生。但作者認為,「歌」也是另一種形式的「意象」。史蒂文森引用了哲學家茱迪斯.巴特勒「受激的言說」的說法,以召喚(interpellation)的概念來表達「我們的生命來自於他人的呼喚,來自於出生時獲得的名字,是名字確保了我們的社會存在」。對作者而言,「歌」是一種能夠超越話語中的命名政治的表達方式。「歌」不但是情感的交流,是超越既有倫理規範與成見的呼喚,是一種主體再現的形式,也是一種陪伴。史蒂文森這個提問,一語點出本書的意圖:「我們能夠想像自己傾聽他人或跟他人說話時不事先固定對方的身分嗎?」
再談生命政治
如前所述,《生命之側》處理兩種「流行病」,其生命政治的手段,在台灣也可見類似的痕跡。讀者或許不陌生樂生療養院的歷史,早在日治時期,透過警察系統執行漢生病感染者的強制隔離,致使早期的樂生院民必須脫離原本的生活環境且終生不得返家。這些血淚斑斑的歷史不只發生在台灣。然而,讀者可能需要注意的是,疾病的治理往往是政治背景、人權理念與醫藥技術共構下的產物。生命政治所體現的,也是在特定的社會脈絡下所形塑疾病的主體性的持續變化。換言之,若不是藥物的發明,隔離措施或許至今也難以得到改善。而成為病人這件事,也不一定是一件難以接受的事;畢竟「疾病診斷」能為受苦定錨,成為改變的起點。再想,我們才剛經歷過的COVID-19疫情,不也再度重現了生命政治的各種價值觀的辯論嗎?也因此,我們確實難以後設的觀點來直指政策的誤謬,只是必須了解,在所有不得不的措施之中,必須覺察策略的有限性,並存乎還要做得更好的企圖。
另外,我在此處想用多一些篇幅討論「自殺防治」。早在十九世紀末,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就以其著作《自殺論》指出自殺與社會的緊密關聯。然而精神醫學發展過程中逐漸主導了自殺的論述,並將自殺與個人的精神疾病加以連結。晚近的人類學研究則再度將自殺置於關切範疇,對社會文化抽絲剝繭,企圖把醫療化的論述再做一番平衡的詮釋。例如,日本的北中淳子寫的《日本的憂鬱》(Depression in Japan)就從日本的過勞與自殺說起,討論將自殺醫療化的可能與困境,簡言之就是人們或許可以透過精神醫學緩解其受苦經驗,並挑戰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中日漸壓抑的勞動文化,但以藥物為主的治療卻無法根本改變受苦者的真實處境。我的博士班老師湯姆.威傑爾(Tom Widger)曾在斯里蘭卡進行研究,他提醒,過去研究自殺的學理往往優先考慮歐美的自殺防治模式,而且時常忽略了自殺是源於地方脈絡下的情境現象。而探索所謂的「自殺文化」,很重要的一點是必須避免對自殺產生刻板的詮釋,自殺所反映現實應該是人們試圖在以對他們來說有意義的方式生活中的掙扎。他認為:「人類學對自殺的研究是一種旨在將生命還給自殺者的方式,並試圖揭露那些被社會權力操作所隱藏的東西。人類學提供了一種獨特的人文倫理方法,試圖在自殺者的死亡權利與其生存潛力之間找到平衡。」確實,我們也能從《生命之側》看見這樣的努力。

Kitanaka, Junko. Depression in Japan: Psychiatric cures for a society in distres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生命之側》所提及的加拿大自殺防治政策,其實並不令人陌生。在台灣,所有的輕生死亡新聞畫面都會加註「自殺不能解決問題」,並附上免費安心專線;這與書中的「匿名專線」相當類似。約莫一九九○年代流行病學家鄭泰安博士進行所謂的「心理解剖」(psychological autopsy)研究,透過對自殺者生前親友的訪談來重建自殺者的生命史,結論顯示自殺身亡者有高達百分之九十七符合精神疾病的診斷。但即使結論如此,也並不意味著自殺防治只能朝向個人化的精神病理的導向。在醫院中定期召開的自殺防治會議,每每皆須統計數字,閱讀報表。我們很難直言這些「把人留下來」的做法都是錯誤的政策。當今的自殺防治仍必須仰賴臨床醫療的轉介、治療、通報,政策上加警語、禁農藥、高樓防墜措施,也合乎公共衛生的科學精神。但真正困難的,是找到能因地制宜並超越個人心理健康論述的照護方式。
照護「未知」之艱難
最後,我認為本書最困難的一點,在於如何從批判的位置中找到行動的方案。作者史蒂文森的後殖民觀點企圖打破政策的誤謬、打破醫療的邏輯,打破讀者對生命的常識定義。她認為因紐特人的生命特質是一種「死活相依」的狀態。以西方或醫學的理性來看,死亡是器官停止運作,一種生命存有的中斷,但因紐特人無法將生死斷然切割,因此那些健康照護與自殺防治政策若漠視了這點,反而使生者依舊經歷了「活著的殘酷」。生命政治在傅柯式的批判下往往被視為個體的主權受到規訓權力的宰制,但最困難的反而是提出更有效的解方。《生命之側》以後殖民觀點對原住民健康提出反省,這樣的批判固然是重要的,但當今的健康治理,本質上仍難以跳脫國家體制,超越政府的框架。
國家對健康是不可能完全放手的,只是做法上確實必須有所調整。首先是KPI導向的績效政治。有太多疾病防治政策往往追求短時間內的數字成效,卻忽略了統計數字背後所反映的深層意涵。再者,疾病防治需要的不是只能提供短暫照面的「專業」與「官僚」人士,而是真正參與陪伴的基層工作者。這些人包括社工、照顧服務員,或甚至可能是難以放入專業框架中的地方協力者。以《生命之側》為例,作者史蒂文森本身並非專業照護人員,但背負恨名的縱火嫌疑青年保魯西卻願意為她歌唱。這無非凸顯了在建制化的體制中的照護關係其實反而可能無法建立信任,甚至受到抵抗;真正的陪伴或許是另一種充滿情緒勞動的工作,照護的果效並不是由專業與技術所堆砌,而是在挫折與衝突累累的陪伴中熬煉出來的。
史蒂文森如此詮釋因紐特人的自殺:「在一個拚命控制未來以擁有現在的時代裡,或許可以將因紐特人自殺視為對缺乏驚喜的未來而有的反應。」對照台灣原住民的現實處境,這種反應「活著的殘酷」的案例比比皆是。同樣用「歌」作為訴說生命故事的方式,台灣原住民的「林班歌」其實也有異曲同工之感。例如〈模範青年〉這首歌,開頭就是「第一個不要喝酒,第二個不要抽香菸,第三個不要吃檳榔……」完全體現了原住民經年接受這種教條式的衛生教育的現狀。然而,歌詞第二段的情緒卻轉了一個方向,直接唱出:「要喝酒嗎喝一杯,三八五八也可以,但願你能記住我的話,我會永遠愛著你。」這不正體現了如史蒂文森所言,透過歌來表達的關心,為他人創造存在的空間,並召喚出主體的目的嗎?
只要活下來就好,對失去生之所依的人來說,反而是一種殘忍。如果死亡本身帶著希望的歸屬,那麼我們還需要做些什麼?這也是本書揭示的難題。但讀者無須誤解本書刻意美化死亡,或是強調健康照護本身必須減工或是放手。重要的是,生命本身的意義往往超越了有限的理性,生之所欲也常常超越了存活的象限之中。這讓我想起在山上進行博士論文田野工作的一個片段。在部落醫療站,一位yaki(泰雅語的祖母)走進來說她身體不舒服,護理師幫她量血壓的過程中聞到渾身酒味。熟諳泰雅語的護理師先與yaki 對話,然後回過頭來跟我說,「你看,這就是我們山上的樣子。」我問,「你們剛剛說了什麼呢?」護理師說:「我剛剛跟她說,再這樣喝下去會死耶,yaki說:『這樣不就更好嗎?』」我常常想起這段對話。從那一刻起,我隱約知道生命之側似乎還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
感興趣的讀者,可以進一步閱讀:
Fassin, Didier, Frédéric Le Marcis, and Todd Lethata. (2008). Life & Times of Magda A: Telling a Story of Violence in South Africa. In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ume 49, Number 2.
Fassin, Didier. (2014). True life, real lives: Revisiting the boundaries between ethnography and fiction. American Ethnologist, 41(1), 40-55.
Kitanaka, Junko. (2011). Depression in Japan: Psychiatric cures for a society in distres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idger, Tom. (2015). Suicide in Sri Lanka: The anthropology of an epidemic. Routledge.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吳易澄 《生命之側》導讀:活著的殘酷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7050 )



回應
* 請注意:留言者名字由發表者自取。
落落長,多言不止。
我想感謝導讀者佛心地為大家整理批判醫療人類學的脈絡,以及民族誌的創新寫法,讓我們有空間去重新看待當地人對生命(與自死)的觀點。
發表新回應